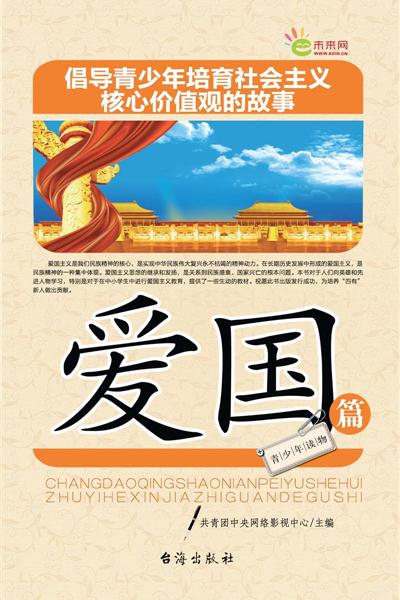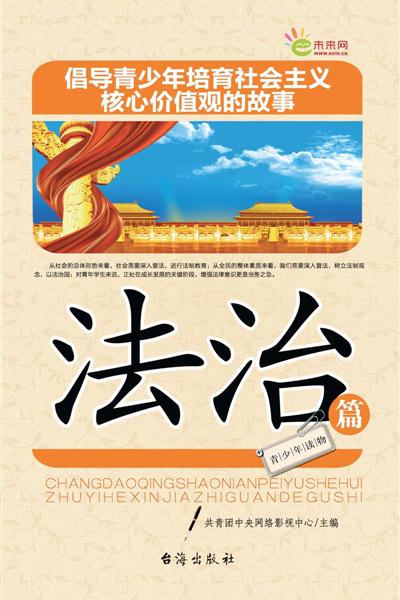简述
邓稼先(1924—1986),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6月,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生平
娃娃博士邓老憨
1924年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邓以蛰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少年邓稼先与杨振宁常常在一起弹玻璃球、比赛爬树。后来,二人先后进了北平崇德中学。
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欢乐的少年时光并不长久。“七七事变”后,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校园里空荡荡的。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咯血不止,全家不得不滞留北平。“七七事变”后的10个月间,日寇铁蹄践踏了从北到南的大片国土。邓稼先
亡国恨,民族仇,都郁结在邓稼先的心头。他也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
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一次,日寇攻陷了一个城市,他们强逼百姓举旗“庆祝”。邓稼先气愤地把小旗子扔到地上,踩在脚下。这事让日本人知道了,找到中学校长。在校长的庇护下,16岁的邓稼先跟随大姐邓仲先匆忙离开北平,辗转来到云南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此前他的好友杨振宁于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本科学习结束后又进修两年硕士研究生课程。
战争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给邓稼先和杨振宁这对好友更多的接触机会。他们俩相差三个年级,可是在野外躲避空袭的时候,却可以随时相伴了。当初崇德中学的一对顽皮小友,这时已成为英姿勃发的年轻大学生,他们的关系依然水乳交融,一起度过了对他们一生都影响深远的三年。杨振宁谈吐中常以天下为己任,同学们俏皮地称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又因他头脑聪明,反应敏捷,外号叫“杨大头”。邓稼先为人朴实忠厚,和善可亲,同学们亲昵地称呼他“邓老憨”。
在西南联大的几年艰苦而勤奋的学习生活,对邓稼先、杨振宁一生都很重要。他们走进了神奇的科学殿堂,窥探到那似乎玄奥无穷的物理学天地的登天小径,也锤炼了意志,并切身体验到国家民族因弱小被蹂躏的痛苦。他们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长大,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声中走上科学之路,也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以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紧密相连。这与他们以后各自的成就都有莫大关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运动,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1947年,他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怀着“今后国内建设需要人才”的明确目标来到美国。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在从事学习与研究的同时,他积极参加了进步留学生团体——“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普渡大学分会”的活动,热切关注着祖国的情况,他被推选为分会干事之一。1950年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邓稼先决心尽快回国。同年6月“留美科协总会”在芝加哥以北的邓肯湖畔举行年会,到会的有33个分会的一百多名代表。会上大家畅谈对新中国的认识,并在篝火晚会上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邓稼先被选入总会干事会两个驻会干事之一,主管财务工作。从邓肯湖边返校以后,邓稼先立即投入撰写博士论文的紧张工作。论文题目是氖核的光致分裂。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完论文,并于8月5日顺利通过答辩,20日参加了颁发博士证书仪式。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他放弃了美国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毅然回来建设仍一穷二白的祖国。同年国庆节,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随后他又深情地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顾及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夫人许鹿希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宅大院和大漠戈壁,一去就是一生。而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长时间也不清楚丈夫具体去向的许鹿希承担大部分家务,坚强地支撑着家庭,使邓稼先得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去。
专心写字的邓稼先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从北京的若干高等院校挑选、组织起了第一批研制原子弹的队伍。1958年秋,他和28名新毕业的大学生来到北京郊外的一片庄稼地里,开始了最初的战斗。作为核武器研究机构的理论部主任,他白天带领大家和建筑工人一起挑砖抬瓦搞试验场地基建,晚上挑灯夜战学习理论,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并于次年撤走全部专家。于是,中共中央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及时向第二机械工业部领导传达了“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决策精神。为了不让人们忘记,“596工程”就成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此刻邓稼先向他的同事们说了这样的话:“研制核武器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国外对我们封锁,专家们也撤走了,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了。我们要甘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还要吃苦担风险。但是,我们为这个事业献身是值得的。”
在没有资料、缺乏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从抓好队伍建设入手。他带领年轻人刻苦学习理论,踏踏实实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尖端科学技术。他坚持读书、备课,为年轻人讲课,并且帮助他们选择学习材料,确定研究方向。他向青年人推荐了当时能够得到的仅有的一些参考书。为了解决人多书少的矛盾和一些人在外语阅读上的困难,邓稼先把大家组织起来,围着长方桌集体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读一章,译一章,译出来后,连夜刻蜡纸油印出来。遇到疑难问题,他和大家共同讨论分析。每晚学习到深夜,年轻人照例骑上自行车,一路上车铃叮当,说说笑笑,簇拥着他穿过乱坟地,一直把他护送到宿舍区胡同口;常常大门关了叫不开,大家就扶着他,翻墙进去。邓稼先常常为了一个问题彻夜不眠,早上用冷水冲冲头,又匆匆走上讲台。有时备课到凌晨,在办公室里睡上两三个小时,又接着开始自己新的一天。
经过将近一年的刻苦读书之后,邓稼先带领大家投入了突破原子弹原理的第一场战斗。他们一开始利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以后才换上了电子计算机)进行理论计算,模拟原子弹爆炸的过程。一项关键数据的计算结果和外国专家的论断发生了明显分歧,邓稼先领导大家反复进行了九次计算。他们一天三班倒,奋战十多个月,验算证明我们的结果是正确的。在邓稼先的严格要求下,各种数据处理扎实可靠。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的全部心思都用到了工作上,走路、骑车还在思考问题,不止一次地连人带车掉到沟里或是撞在电线杆上。一次,他连续几天没有好好休息,实在累坏了,竟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重心一偏,摔到地上,他居然都没有醒来,反而在地上舒展开四肢,越睡越香。还有一次,他指导年轻人查阅资料,教他们计算方法和写理论计算报告。讲完了,微笑着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自己却站在那里睡着了。不一会儿醒来,他不好意思地问自己睡了多久。年轻人笑着告诉他:“才一分钟,你不过是站着打了一个盹儿。”
1964年10月,神州升起第一朵蘑菇云,全国为之欢呼雀跃。但由于邓稼先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巨大的功绩连最亲近的家人也无从知晓。当许德珩老人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曾兴奋地向严济慈先生说:“咱们中国能自己造出原子弹来,不知道谁有这么大的本事?”知道内情的严济慈哈哈大笑,回答说:“去问你的女婿吧!”
而当整个核试验基地还处在一片欢腾之中时,邓稼先已登上前沿指挥车,冲向爆炸中心。在他和其他一些同志聚精会神地审读着各种第一手的数据资料时,他被告知母亲病危,要他立即返京。为了原子弹爆炸,这个不幸的消息不得不被压到此时才让他知道。邓稼先日夜兼程,赶回北京,直奔医院。母亲看到儿子,把刊登着原子弹爆炸的套红的人民日报从枕边拿出来,她不责怪儿子的晚来,只是说他应当早点让妈妈知道他的工作。在这之后,母亲就安详地睡去了,仿佛这最后一刻的弥留全是为了等待儿子的到来。
签原子弹零时起爆的人
原子弹起爆前的信号是倒着数的。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爆!这个起爆时刻,干这一行的人把它称作零时。
每一次核试验的零时之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一无所知的,这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和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零时之前,对于参加试验的工作人员来说,却是一个充满期盼的不平凡的日子。他们盼望准时看到自己的劳动化为蘑菇状烟云升腾到湛蓝的天空,巨大的火球不断翻腾,颜色在不断变化,像巨神拿着一颗宝石在转动,五颜六色,光彩耀人。而如果是地下核试验,那就是两声闷雷似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深井之下,另一声是来自背后大山的回声,惊天动地,滚滚而来。但是对于一个签署者来说,零时之前又是一段特别难熬的日子。在核弹制成之后,邓稼先夫妇准备用飞机运去空爆或是进入深井做地下核试验前夕,要有一个负责人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这一核弹的试爆准备工作已经一切就绪,可以点火了。这是对祖国负责的签字,非同一般。在邓稼先生前,这副千钧重担大多数由他来挑——签字署名。
每次核爆零时前对于签署者的煎熬是异乎寻常的。在原理方面一点儿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的问题搅着签署者的心。邓稼先在每次核爆签字之后都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全身冰凉,这样重的心理压力几乎使他坐立不安。每逢核试验前,他都来到场地,表面上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一个每临大事气定神闲的大将风度,其实这是为了稳住大家。但实际上,应该说从此他就天天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他在帐篷里时而复核着突然想到的某一个尚无完全把握的数字,时而又愣神坐在那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究竟在想些什么?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的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够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邓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零时之前对签署者的压力,一般人难以想象。对于责任心极强的邓稼先来说,这种说不出来因而也就无从下手去补救的担心,更是终日伴随着他。邓稼先曾开玩笑似的说过,签字以后,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然而他的脑子还能正常地工作。有一次睡到半夜,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于是从自己的铺位上一跃而起,叫醒了几个帐篷里的人,连夜商量对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
准备核试验的前期,有时候他们要在马兰待上几天。马兰是为了进行核试验才盖起来的小镇子,因这里的沙漠地上有一种马兰花而得名。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就载有这种花的名字。马兰花呈雪青色,花心上嵌着一支白色的条带。在这干枯、单调的戈壁滩上见到马兰,使人能暂时得到一种生机盎然的情趣,同时也会使人产生一种联想,想到大自然似乎也有一种爱美的天性,有机会就要打扮一下。邓稼先每次在马兰小镇散步的时候,看到这种朴素的小花,就觉得自己被各种牵挂裹紧了的心能稍微放松一下。这种调剂对参试者的身心是大有好处的。在邓稼先的家中,他的亲人为了纪念他,安放在他大幅彩照旁的,一边是一棵青松,另一边就是一棵马兰。
邓稼先夫妇与杨振宁的合影
就是住在试验场地帐篷里的时候,邓稼先也要忙里偷闲。一有空,邓稼先就和李医生一块到戈壁滩上去抓呱呱鸡玩。这种有着灰色长尾巴鸡,样子并不美。但对于整日里提心吊胆和数字打交道的人来说,能去追着呱呱鸡连飞带跑,就是极大的快乐,他们似乎又回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着活力和兴趣。但他们这种梦境般的欢乐,很快就被后方传来的一个惊人消息给搅掉了。邓稼先的心好像从轻松的高处直线下坠,他浑身的肌肉好像完全僵死了。后方急报说计算结果中有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应该停止这次核试验。这不啻是晴天霹雳,猛然轰击到邓稼先头顶。邓稼先只觉得大事不好,他们很快乘吉普车来到竖井处。李医生发现邓稼先的脚步忙乱,怕他出差错,便飞身转到井口梯边,扶住了邓稼先。他下井检查完应该检查的一切,便回到帐篷里沉思起来。轻易地停止核试验,问题可就大了。但如果试验出了问题,后果更不堪设想。现在是一个需要深厚科学功底的当口。
为了此事,邓稼先在井上井下来来回回地忙了两天两夜。这两天,由于紧张,他几乎隔一小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他用各种办法去推算,从多种角度去核查,拼命想寻找出一种证据,证明能够继续试验。因为要是停止这次试验,起吊装好雷管的核弹本身就是极危险的事,何况还要卸去已拧死的螺丝钉,才能改动装置。但是可靠的证据一时寻找不到,他又躺在了铺上,两眼望着帐篷顶子,似乎想稍稍休息一下。突然,他想到中子不带电荷这个他在初中时早就知道的常识。一个普通常识,在解决重大科研难题时竟变成了一把金钥匙,由此打开了他逻辑推理的通道。他用纸笔又一次做了粗估,判明计算即使有错,误差的幅度不至于大到影响核试验的成功。最后,他得出结论并拍板:核试验可以照常进行。结果是这次试验完全成功。
致命的伤害
研制核武器除了连续作战、费尽心思地用脑非常伤身体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东西,那便是钋239和铀235的放射核辐射对人体的伤害,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着新的核试验。他经常出入车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其辐射。干这一行的人把这种事叫作“吃剂量”。说得如此轻松,丝毫不带感情。大概他们是为减轻辐射伤害对人类带来的精神负担才有意这样说的。有一次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的结果,原有的防护措施挡不住放射性能极强的新材料的射线,使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这样超限度的“吃剂量”,后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所有的工作都照样进行下去。邓稼先自己对此并不太在意。
但是,不得不令人在意的事终于到来,事情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军工事业深受“文革”十年动乱的破坏,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核试验时,一次偶然的事故出现了。邓稼先决定亲自去现场,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基地司令员陈彬同志也阻挡他。其出语非常感人,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为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不听这位司令员和同志们的多方劝阻,决定立即上车。他心里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事我不去谁去?”他一向是这样做的。他平时对于别人的安全非常关心,而偏偏把自己的健康和生死置之度外。这种拧脾气,似乎是从事核武器研究之后添的“毛病”。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没有说话。但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顾得想想放射性元素对人体的伤害。他一定得找到它,探明原因。
邓稼先旧居
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跑,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他们九院的宝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感。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与他同行。最后他急了,忘掉了对领导同志应有的尊重,他大声对赵副部长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是一句只说出一半的话。如果把这句话完整地说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白白地做出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有必要干什么呢?
这位50多岁的核科学家、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总负责人勇敢地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了。邓稼先已将刚才想到的对人体的伤害忘得一干二净。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勇敢,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英雄行为。大概所有真正的英雄都是这样的,他完全和平时一样,只不过有一份急切的焦虑心情。他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锐利的目光四处扫视,边走边找。终于,碎弹片被他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傻子,他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危险的放射物。他立即放心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的精神骤然松弛,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远方的吉普车走去,他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就在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是有事了。于是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至今,在邓稼先家中的相册里仍有一张只见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自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类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却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的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元素的辐射伤害,这将是他身体健康的巨大转折。
此次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他可以避免这一次致命的伤害吗?他应该躲过这一次致命的伤害吗?和他共过事的熟人、了解他的朋友在他逝世的许多年后,仍然对这个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一定会去的,这是他世界观发展的逻辑结果。在他冲进去的时候,受到责任感化作的强烈情感的驱使,他想不到别的事情,他顾不得。他脑子里只想赶快知道事故的结果,个人安危他来不及考虑。这,就是邓稼先。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物,白血球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数量虽在正常范围,但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但他只对妻子许鹿希说了尿不正常。这让许鹿希火了,跺着脚埋怨他。按道理邓稼先应该到疗养院去,受的放射物剂量这样大,疗养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身体无疑有很大好处。可是他没有去,他离不开工作,直到他离开人世之前,他没有疗养过一天。有一天晚上,许鹿希耐心地坐在身旁劝说他。邓稼先斜倚在床上,他宽大的上身靠在厚厚的被褥垛上边,两手交叉枕在脑后。他的眼睛,时而看着妻子,在听劝说;时而愣神望着墙板,在想别的。是什么想法把他的眼神拉过来,又是什么想法把他的眼神推过去的呢?许鹿希能猜得到,因为她毕竟太了解他了。邓稼先的心在事业上,他为自己健康忧虑的落脚点也在事业上,身体是搞好事业的本钱。自从他投身到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研制工作以来,我国的核武器便以很快的步伐前进。从绝对速度讲,我们的速度甚至超过了超级大国,这一点是令全世界震惊的:从制成原子弹到制成氢弹,美国的间隔是7年零4个月,前苏联4年,英国4年零7个月,法国8年零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1964年10月到1967年6月),并且研制氢弹最后一年的工作还是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中完成的。
邓稼先自从那次“吃”了大剂量,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很快,头发白了,工作疲劳也不易消除。打从小时候起,他是非常喜欢出去玩的,但这时却已是力不从心。有一次大家爬山,半路上他突然感到举步艰难,身上沁着虚汗。最后,这次郊游就半途而废了。有时开着会他突然感觉心跳很快,于是便把手伸给高副院长,让老高帮他搭搭脉,这时他的心跳每分钟已经超过120次。有时他甚至非常怕冷,他觉出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或者退下来,争取过几年安生日子,延长一点儿寿命,并补偿一些对妻子和孩子所欠下的感情债。自己也该喘息一下了。他的确感到肩上的工作担子使他过分吃力,科研攻关时要绞尽脑汁和耗尽精力;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相互矛盾的要求,常常让人顾此失彼;因被别人误解和其他的伤害,令人有时感到心情沉重。他偶然间想起卢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块瓦片从房顶上落下,是有可能伤着我们的,但不及坏人蓄意掷过来的石头伤及人的心。”总之,过去这些他不甚介意的东西对他心灵的刺激比以前是稍微加重了一点儿。他在各方面都显出了疲劳的痕迹,身体的和心灵的。
一次,他利用散会后的一点空暇,和妻子到颐和园去。颐和园是他们俩玩过多次的地方。园里的山山水水,从佛香阁到十七孔桥,还有湖的西岸边未经修整的野路,他们都是很熟悉的。每次游公园、逛商场、看庙会,他总是兴致勃勃,这一次也是他出的主意。那天他们原打算看菊花展览,等他们赶去时,展览已经关门,这是晚霞斜挂西山的时候了。园内的喧嚣声随着游人慢慢离去而渐渐消失。他和妻子漫步走在后山的小路上,路旁低处的土地上有星星点点的小花,俩人的步子不约而同地慢了下来。还没有走到最高处,邓稼先便觉得有些累了。他们在铺满秋叶的路面旁边选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大石头,邓稼先马上坐了下来,这时许鹿希剥了一个橘子递给他。斜阳的余晖下,万寿山此时格外安静。邓稼先吃着橘子,似乎是漫不经意地浏览着湖光山色。忽然,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多恬淡、多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他对安静优美的大自然、对夫妻间悠闲自在的生活,流露出内心深处的一丝眷恋之情。
1984年年底,邓稼先指挥了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组织指挥的一次核试验。邓稼先在严寒中又一次来到罗布泊这度过一生中那短暂难熬但又异常兴奋的地方。在1986年前,国家进行的核试验中,他亲自在现场主持过近一半。这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有人称邓稼先是福将。福将,习惯上的理解无非是老天爷保佑。那么多次那样复杂的核武器试验全都靠天行吗?当然不行。这只能是邓稼先本人的水平和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结果。老天爷可帮不了这么多忙。由于常常在罗布泊基地工作,他对这一块楼兰古国旧址,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特有的荒漠旷景是和他事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连在一起的。这年年底,他已经满60周岁了。邓稼先壮年不壮,因为就在几年前,他所受到的严重辐射损伤,一天天耗掉了他体内的生机。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带着自己魁梧而又极为虚弱的身体来到基地,但国家对这一次的试验有重大的期待。
试验前夕他接连几天都在拉肚子,大便带血,步履维艰,而他自己却以为是痔疮出血加血糖病。结束试验时,他在前沿指挥车上急切地等待着结果。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当他看到所预期的实验波形时露出的兴奋笑容,但无情的病魔早已侵入了他的躯体。1985年,邓稼先在北京参加会议时,才在夫人的催促下抽时间去了医院。通过检查确定为直肠癌,需要立即住院手术!张爱萍将军亲自主持了医疗小组的方案讨论会。邓稼先先后两次住院,三次手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在他住院的一年间,杨振宁曾两次前往探视。第一次探望时,邓稼先精神尚好,还可以站起来迎接老友。俩人谈兴很浓,他们一起回忆往事,互相询问熟识朋友的近况。杨振宁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随手写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图。分别前,俩人在病房里合影留念。然后邓稼先执意送杨振宁至病房门口,并要许鹿希代他送振宁下楼。在杨振宁上车前,许鹿希告诉他说,邓稼先病情已非常危险,几乎无治愈希望了。这消息给杨振宁很大打击。他为老朋友的病情焦虑不安,在美国找寻治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可惜药送到后已为时过晚。
1986年6月13日,杨振宁回美国前又来看望邓稼先。此时邓稼先开始大出血,医生已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杨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卧床不起的邓稼先,气氛惨然。杨振宁送上一束极大的鲜花,他知道,这次可能是与老友的诀别了。邓稼先的神智还很清醒,在杨振宁走后,他对妻子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来特大的一束鲜花……”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就在几天后,1986年7月29日,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
总结
邓稼先,一个矍铄的科技泰斗,以其血肉之躯,扛起了共和国的核事业。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
如今,邓稼先已成为了时代的楷模,人们学习的榜样。的确,这种忘我无私的爱国精神,确实值得弘扬。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涌现出更多像邓稼先这样的科学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