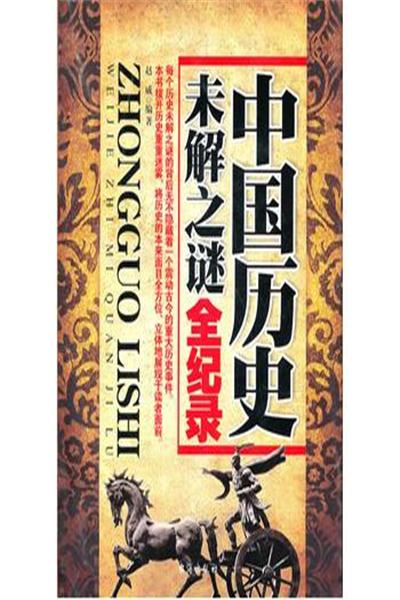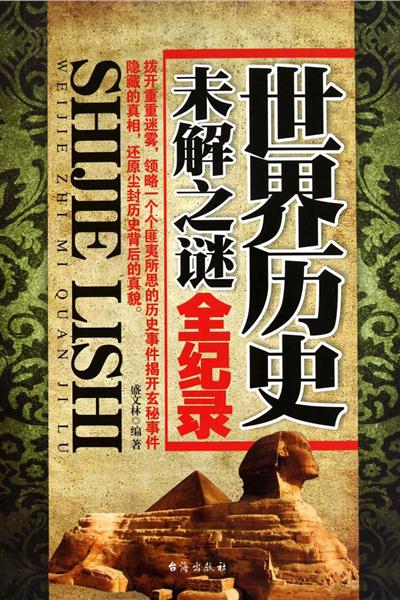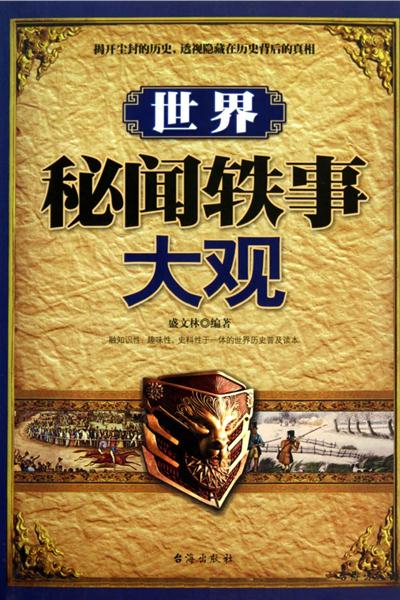香港九龙约道五号,一幢濒海花园洋房,是周佛海的寓所。因港英政府明令禁止民间有枪,周佛海只得花钱从九龙镖局雇来两个彪形大汉看家。一个大汉手持一把汽枪守卫大门,另一个大汉怀揣匕首整天在园内巡逻。在香港,这也算得上是戒备森严了。
这天天气很好。
从早晨起,周佛海就安静地坐在二楼他的书房里,透过落地玻璃窗,似乎很有兴致地观赏外面的风景。维多利亚海湾将九龙与港岛隔了开来,两边各有各的景致。海湾对面的港岛上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尽显国际大都会风采。海湾这边的九龙则处处点缀着田园风光,赏心悦目。香港的地理位置太好了!维多利亚海湾虽然宽不过一里,但是优良的深水港,万吨巨轮可直接开进港湾停泊。澳门就不行,澳门是浅海,因此经济发展远远比不上香港。
香港的心脏——寸土寸金的港岛上,还有一处得天独厚的太平山。从落地玻璃窗中望去,绵延青葱的太平山,像是一匹扬鬃奋蹄的骏马,横跨在港岛南北两端。住在太平山上的都是家资上亿的高官巨贾。山上冬暖夏凉。当绵绵的季风起时,太平山是港湾中的轮船最好的屏障;太平山不仅是富人的天堂,也为居住在香港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数百万居民提供了庇护。
太平山最初叫扯旗山。它是港岛上的地势最高处,山上啸聚着一帮盗匪。每当有商船进港,若是觉得值得抢,时机也好,就会在山顶上扯起旗帜,发布信号,召唤盗匪们下山抢劫。香港成为了英国人的殖民地后,港英政府好不容易整肃了山上的盗匪,为粉饰太平,将扯旗山改名为太平山。地产商们不失时机地在山上修建起一幢幢高规格的别墅。很快,太平山成了香港上流社会人士集中聚居区,住在山上的有港英总督、空军司令、赌王、富商……跨入二十世纪后,港岛与九龙间修起了两条海底隧道,一条是政府的,一条是私人的,车辆过往更为快捷方便。
周佛海觉得,他从河内陡然来到香港,就像是从农村进入了繁华喧嚣的大城市。香港,连风都是香的。特别是,蓝天白云下,维多利亚海湾对面的港岛上,幢幢造型别致的华美大厦,利剑一般直指云霄,那些特制的玻璃幕墙在明丽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与之隔海相望的香港文化中心又是那么的恢宏。世界著名的米黄色的半岛饭店,象牙般地精致堂皇……住在这座人间天堂里,周佛海有种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恍惚感和幸福感。
视线所及中,绿色绸缎般的维多利亚海面上,一艘艘有钱人家的豪华游艇,或乳白,或淡黄,或天蓝……像是一只只雍容华贵的天鹅,滑行在海面上。
当周佛海的目光转到烟敦山时就不动了。山上那座烽火台还保留着古老的遗风,有缕缕白烟从中升起来,被风扯着,向东飘去。他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汪精卫乘坐的“北光号”,今天下午或是明天上午会经过这里,向上海驶去。“北光号”不会在香港停留,因此他也不必去同汪精卫见面。汪精卫海上遇险,他是从影佐副手,“梅机关”重要人物今井武夫那里得知详情的。后怕之余,他暗暗庆幸,自己这会儿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坐在香港小洋楼里观山望景,全靠自己脑瓜子灵。在河内,当他一听陈公博带来的蒋先生的话,就听出蒋介石这是先礼后兵,要出事,出大事。数月前还是重庆国民党大员,国民党特务机构CC高级领导人的他,对蒋介石的阴险、狠毒是太了解了。如果不是逃得快,说不定像曾仲鸣一样,当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在暗暗庆幸自己逃过一劫的同时,周佛海的思维很快转到了当前的局势以及如何应对的思考上。毫无疑问,要抓紧时机抓钱抓权抓人,搭自己的班子。汪精卫和他是在互相利用。目前,汪精卫、陈璧君是在唱夫妻双簧戏。汪精卫在前台发号施令,陈璧君则在后台组织陈家班——以陈春圃、陈国琦为骨干的“公馆派”。他们招兵买马,壮大势力,希图在未来的中央政权中攫取尽可能多的关键席位。作为“公馆派”中参谋总长人选的陈璧君,周佛海内心是看不起的。在他看来,在未来自己同公馆派的斗争中,真正的对手是至今还没有出场的陈公博。别看现在陈公博同汪精卫政见不合,一怒而去,但他早迟会站在汪精卫一边而且要挑起大梁的。他太了解陈公博的性格了,也太了解陈公博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了。
周佛海想起一句西方哲语:在这动乱的年头,要紧的是两眼盯着自己的鼻子,尽快将自己的根基夯实!汪精卫不是让我搞钱吗?我就借此由头尽量搞钱,只要手中有了钱,就会有一切!
周佛海一到香港,找到“志趣相投”关系也深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一说。唐寿民很快就给他送上80万元。唐寿民心中明明有把锯锯镰,可嘴里说得蜜蜜甜:“汪先生勤劳国是,需款必殷。我们在此略表微忱,以申敬意。但求为我们严守秘密,以后我们再当筹款敬献。”——未雨绸缪,两面讨好,脚踏两只船。对唐寿民这些买办阶级的特征,早年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真是太了解了。
周佛海在历史上同汪精卫有过龃龉。他们现在之所以走到了一起,除了政治上臭味相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奔,需要互相利用。周佛海需要的是借汪精卫这块招牌,设法将“和运”变成自己的股份公司;汪精卫则需要周佛海的经验、关系和找钱能力。周佛海清楚汪精卫性格上的弱点——做事向来“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年屡遭失败”,且“无担当、作事反复、易冲动”。相对比较起来,难对付些的是汪精卫背后的陈璧君。
周佛海在心中暗暗计算他到香港后收罗到手的人。在军事方面有叶蓬,其人担当过蒋介石的武汉警备总司令;杨葵一,清末留日武备生,在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曾在武汉国民党行营当过参谋长。文人方面有樊仲云,其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务,是一个以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相标榜的十大教授之一,当过星岛日报主笔;罗君强,是他的湖南老乡。早在抗战前,因为周佛海的提携,罗君强便官拜国民党大本营(军委会)少将秘书。抗战期间,在武汉,罗君强在交际场中认识了一个叫孔小姐的美人,为敷开支,贪污了一笔巨款。事后,罗君强脚底板抹油溜到香港,被他收罗门下。此外,还有一个专门从日本回来依附于他的作家周作人……
周佛海正在沉思默想时,门上湘帘一掀,夫人杨淑惠进来了,吵嚷着说:“我们不是讲好了要去香港海洋公园的吗?你看看几点了,怎么在那里不动呢!”杨淑惠指指自己戴在腕上的金壳坤表,噘起嘴,“都十点了!”杨淑惠显然是打扮过的,穿了一件黑丝绒旗袍,纹了眉,脸上扑了粉,唇上涂了口红。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但毕竟是人到中年,本来丰满高挑的身材有些发福,旗袍在身上箍得又紧,开叉又高。这样,浑圆的乳峰、肥大的臀部显得太突出了些。走动间,两条肥腿不时亮出来,白晃晃的。周佛海看在眼里,不禁皱了皱眉。
“好,走、走!”周佛海虽是一个强人,但有些惧内,不太情愿地站起身来。
周佛海夫妇带一个保镖,驱车来到了举世闻名的香港海洋公园。下车后买票进入公园,只见一座秀丽的山峦傍着维多利亚海湾拔地而起,山上遍披青翠,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硕大青鸟。他们登上九级台阶,进入缆车站。只见空中高架上托起的两根长长缆索上,一个个红红绿绿装了游客的椭圆形玻罐,在空中滑来滑去,交错不断;游客们把爽朗的笑声洒在空中。这时,一个绿色漂亮的椭圆形玻罐从空中滑下来,停在了他们身边,罐门自动打开。周佛海夫妇带着保镖进入能容六个人的玻罐坐好,罐门自动关闭。倏忽之间将他们举到半空,在那条足有三、四华里长的空中索道上滑了起来。透过透明的特制的弧形罐壁望出去,一幅幅美景展现眼前。脚下是渐次展开的波光粼粼的大海,头上是万里蓝天,漂亮的缆车带着他们,嬉戏于蓝天、苍山与大海间。周佛海感到少有的心旷神怡,杨淑惠乐得开怀大笑,银铃似的笑声在空中传得很远很远。
终于,缆车稳稳地停了下来,他们从空中回到了人间。罐门开处,他们鱼贯而下,沿着石板甬道,在鲜花丛中穿行。他们去到了百鸟园,然后再到海洋馆。沿着特制的透明的管道向大海深处走去。身边海洋中那些五光十色的珊瑚鱼、形态可掬的海狮、体形庞大性情憨厚的鲸鱼、凶猛的鲨鱼……无不在身前身后碧绿的海水中游弋、沉浮,似乎伸手可及。
走出透明的海中管道,他们这就上了另一座绵延青葱的山峦。步换景移,视线中,过山车呈360度在空中猛冲旋转,惊险刺激……他们去了海洋剧场,在台阶上坐了下来。从密密麻麻的人头往下望去,远远地,山下一湾碧潭中,一只杀人鲸正在作惊彩表演。随着驯养员的指令,它忽而跃到岸上,用嗜支起身肢,昂起头同人接吻;忽而像只炮弹“咚!”地投入水中,炸得水花四溅;忽而,一只海豚从碧波中跃起来钻圈、衔球……煞是有趣。节目精彩纷呈,场上掌声不断。
高潮出现在美国高空跳水队表演。碧潭边上支起一根极高的高杆,高得让人仰起头看,危得让人噤着呼吸。高杆顶上又是一根横杆,整体看,很像是当年蒙难的耶稣戴在胸前的十字架。倏忽间,高架上站了三个人,小得只有三个黑点。周佛海从保镖手上接过望远镜看去。蓝色天幕的巨大背景下,在架上最高一点上站着一位身着三点式金发白人姑娘。稍下,横杆两边一边站一个铁塔似的黑人,真是黑白对比分明。姑娘轻舒双臂,脚一蹬,头朝下,在空划出一道优美的孤线,像只紫燕钻向大海,她身边的两位黑人跳水队员也动作整齐一头栽了下去……高杆那么高,他们脚下的碧潭那么小,稍有闪失不得了。周佛海不由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望远镜中,一白两黑三位跳水队员前后准确地钻进小小的碧潭,溅起三朵高高的水花……周佛海正在心中好生感叹,有人在背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周先生、周先生!”他一惊,和坐在身边的保镖调头一看,不禁睁大了双眼。
“啊,是翦建午翦先生?”周佛海用眼色制止着保镖不要乱动,“巧了,你怎么也在这里?”翦建午原是他的属下——国民党特务组织CC中的一个中层干部。
“我早就听说周先生到香港来了。”翦建午藏头露尾地说,“我一直在找你,好容易才在这里找到周先生。”看周佛海满脸惊惶,西装革履的翦建午不怀好意地一笑,“周先生,我们是不是到外面去谈谈?”
周佛海怀疑眼前这个翦建午是重庆派来暗杀自己的特务。猛地一惊,林柏生被重庆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砍头的恐怖场面闪现眼前。他知道,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手中的CC——中统,在香港有个暗杀团。前天,汪精卫的外甥沈崧就是被中统暗杀了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一边在心中埋怨杨淑惠纠缠着让他来海洋公园,一边不由翦建午分说,拉起杨淑惠,在保镖护卫下匆匆走了。
随后两天,周佛海一直猫在家里,哪里也不去。想着香港的不安全,他就忐忑不安。
第三天一早,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竟寻到了他家来。在客厅里坐定,一副文人打扮,人精瘦、戴眼镜、穿西装打领带、唇上护一绺仁丹胡子的总领事略为寒暄,站起身来,双手递给周佛海一封电报。然后又是鞠躬如仪地端坐。周佛海狐疑地接过电报,电文很精短:
“典,我已抵沪、速归。昭。”
这是一封汪精卫由上海拍来的电报。“典”是周佛海近期的代号。“昭”是汪精卫的代号。其余的“首义”分子都有代号:陈璧君是“兰”、梅思平是“福”、高宗武是“深”、陈春圃是“农”、林柏生是“琸”。仅管陈公博拂袖而去了,但汪精卫也给他取了代号等着他归来,陈公博的代号是“群”。
在接下来交谈中,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中村丰一,引用了一句中国的成语“闻鼙鼓而思良将!”他人虽然显得斯文,但金丝眼镜后的眼神像出鞘的利剑,颇有深意地笑了一笑:“汪先生一回到上海,风尘未洗,就来急电召周先生回去,足见汪先生对足下的重视。足下是汪先生身前独当一面的良将、大将。不知周先生帐下的兵马是否物色齐备?”
不用说,这位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是代表日本军部来同自己谈话的。周佛海言谈举止清楚地掂出了中村的分量和来意。
“实不相瞒!”周佛海略为沉吟,说了下去,“我现在别的人才不缺,紧缺的是一位特工人才。上海虽在贵军的势力范围内,但因为有租界,蒋介石的特工在那里十分猖厥。我们如果没有一位得力的特工人才,尽快组织起一支有相当保护力的特工队伍,那么,不要说我们没有办法开展工作,连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
中村丰一频频点头。
“周先生,”中村说,“我今天来,主要就是向你推荐这样一位人才。”
“谁?”周佛海陡然来了精神。
“周先生,你认识李士群吗?”
“啊,李士群——认识。”周佛海说时,头脑中立刻闪现出一张四四方方的青水脸。时年34岁的李士群堪称精干,中等身材,寡言笑,体格结实匀称,一看就知是经过训练的。素常穿一套麻格格的劣质西服,看人目光凌厉,动作敏捷,是个特务的料。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农家出生。早年在上海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中共送去苏联接受特工训练,1928年回国后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CC秘密逮捕后叛变。过后,李士群和另外两个与他有相同经历的共产.党叛徒丁默邨、唐惠民臭味相投。他们合伙在上海租界白克路办起一家社会新闻周刊,为掩人耳目,他们伪装进步,在报上发表文章大肆抨击汪精卫。李士群为人阴险,脚踏两只船,一边向国民党CC出卖情报,一面又向共产.党表示忠诚。不久,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怀疑李士群,为了考验他,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秘密处决丁默邨。可是,李士群当面答应,转过身却将这个秘密向他的“丁大哥”和盘托出,作为加深他和丁默邨友谊的礼物。然而,怎么向共产.党组织交待,以便自己继续在共产.党内混,捞到尽可能多的好处呢?他想好了一条毒计。
1937年一个晚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绰号马大麻子,同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愧,还有丁默邨,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高等妓院出来时,已是深夜。深深的弄堂里万籁无声。这时,李士群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笑嘻嘻地向他们迎上去,在醉眼朦胧的马大麻子肩上一拍后,赶紧同丁默邨避开了去。黑暗中两声枪响,马绍武应声倒地而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闻讯大惊,严令上海有关当局限期破案。案子很快破了,丁默邨、李士群同时被捕。因为丁默邨有他的至交好友、CC高级特务、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获释,李士群却大吃苦头。他被押到南京受尽酷刑。看来必死无疑,幸好李士群的妻子、长他五岁的叶吉卿闻讯后变卖家产,赶到南京,用重金贿赂中统高级人物马啸天、苏成德、顾建中、徐兆麟等,李士群的死刑案被放了下来。趁热打铁,叶吉卿最终走通了CC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表弟——关键人物徐恩曾的路子,李士群这才转危为安,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还在中统上海行动股股长马啸天手下重操旧业,当了一名侦察员。只是中统规定他不得擅自离开南京,算是对他限制使用。李士群干特工有一手,而且在新东家面前也确实卖力,因而,他很快得到主子的赏识,在中统内混到了中层干部职务。抗战时,他奉命到上海审判一名日本女特务,却沉迷女色,被日本女特务拖下了水,离开组织溜去了香港……
想了想,周佛海问中村:“李士群不就在香港吗?”
“现在他又回上海了。”中村说,“他到香港后,在我手下做情报工作。这个人年轻、精明能干、又是从重庆那边杀出来的,对那边的情况熟悉。在未来同重庆的激烈斗争中,李士群是对付国民党以及共产.党的最佳人选。”
周佛海深感日本人虑事之周密。确实是这样,他想,李士群既是共产.党营垒中的叛徒,又是国民党营垒中的叛徒,这个双料叛徒对国共两党的特工情况都熟悉、确是我们这方特工的最佳人选。于是,他说:“谢谢,中村先生真是雪里送炭。”对他来说,李士群无异是他回上海前夕,日本人送给他的一份厚礼。
太阳刚刚升起。苏州河的浊水被阳光幻成了金绿色,静悄悄地向东流去,注入大海。黄埔江正在涨潮。晨风送来外滩公园中播放的音乐,是软绵绵的何日君再来。这种让人骨头都快酥了的音乐,与当前紧张的时局完全是格格不入。缕缕晨雾笼罩了外白渡桥上高耸的钢架。
“哐啷啷!”电车从桥上驶过时,空中不时爆出几朵碧绿的火花。浦东一排排洋栈像是蹲着的一头头怪兽。向西望去,一幢幢插入碧霄的洋房顶上,霓虹灯管闪射着火一样的赤光、青鳞似的绿焰;“仁丹”、“富士山”……招牌时隐时现。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雪铁龙”轿车闪电般过了白渡桥,向西一个转弯后,沿北苏州一路急驰。坐在车内的汪曼云,听名字该是个妙龄女子,其实是个身材健壮的中年男人。汪曼云轻声问坐在身边穿中山服、戴博士帽绅士模样的章正范:“李士群说好了在家等我们的吧?”
章正范没有说话,只是肯定地点了点头。
身着长袍、头戴博士帽、长不像葫芦、短不像冬瓜的汪曼云爱笑,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但俗话一句,“笑官打死人”。这个爱笑的汪胖子才不是个简单人。他原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日军占领上海后,他惶惶然不可终日,想另找靠山,这时,他的把兄弟章正范找上了门。章正范原来也是吃国民党的饭,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同时又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门生。章正范告诉汪曼云,现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投靠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李士群。汪曼云听了求之不得。于是,章正范在电话上同李士群说好后,又约了时间,这就带汪曼云去见李士群。
“李士群对我的情况是清楚的吧?”在车上,汪胖子似乎有些不放心,问章正范。
“清楚。怎么不清楚呢,大家都是在上海滩上混的人嘛!”章正范言在此而意在彼,给汪曼云吃了一颗定心丸。说着,大西路67号到了。汪曼云下车后用职业的眼光一看,暗暗佩服李士群。李士群住的房子很有讲究:地处租界边缘,视野开阔。若有刺客来,在房外无藏匿之地。特别是旁边紧邻着一座美国兵营——无论如何,重庆暴力团是不敢为杀一个李士群而去惊动美国人!
章正范上前按了门铃。稍顷,里面石板甬道上一个大汉沉重的脚步声响了过来。
“叭嗒!”铁门上开了一道小窗子,贴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啊,是章先生!”认清站在门外的是章正范,门开了。开门的,不知是李士群的保镖,还是李士群发展的第一批打上了“汪记”的特务,其人苏北口音,身材健壮、穿身黑色纺绸宽松衣裤,一张紫酱色的四方脸上,有许多小痘痘,络腮胡子,手脚粗大有力,眼睛里的光枪弹似的又冷又硬。章正范客气地给双方作了介绍,汪曼云记下了这苏北口音的家伙名叫张鲁。
两人进了门,刚走到主楼前,李士群已迎下楼来。听了章正范的介绍,李士群很热情地同汪曼云握了握手,一边说:“汪先生我是知道的,知道的。”他们上楼进了客厅坐下后,佣人送上茶水点心,轻步而退,并轻轻带上门。
“幸会。”李士群同他们两人寒暄之后,直奔主题,“可能汪先生已经知道了,我现在为日本人做事……”汪曼云心想,他不说自己为汪精卫做事,而是说为日本人做事,是标榜自己的后台大,靠山硬!只听李士群继续说下去,“之所以如此,一是为报复CC。想当初,他们对我李士群手段何其歹毒!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二是想利用我这点本事,在日本人手上弄上二、三十万块钱溜之大吉,哪管你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说着,他看了看汪曼云的反应。汪胖子大智若愚地笑着。
“我和章先生是朋友,现在同汪先生也是朋友。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以后,我们互相帮助!”李士群的话就说到这里。汪曼云看李士群的话说得欲露还藏,便点了一句:“李兄想必清楚,现在租界虽是外国人的,日本人虽不敢怎样,但毕竟已是海中孤岛。”他指了指章正范,“若是我们这些过去吃老蒋饭的人被日本人拿着,李兄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没有问题。”李士群说,“只要你们说是我李士群的兄弟,日本人就不会怎样你们的。”
“那李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在日本人那边是什么地位?”汪胖子很好奇,来个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心想,这个李士群一脚刚刚才踩进汪精卫的圈子里,难道又一脚踩到了日本人那里?这个李士群的“水”究竟有多深?
李士群说:“我在日本人那边挂了个特务机关长名义。”
“啊!”汪曼云听到这里,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下定了决心投靠李士群。因为是初次相见,话谈到这里,汪曼云用眼色同章正范会了一下意,就起身告辞。李士群也不挽留,只是很客气地将他们送出大门。
就此开始,汪曼云、章正范就算正式加入了李士群的营垒,不过相对独立;尽可能送些情报给李士群。李士群在他们面前也不做出一副上司相,之间不时酬酢往来。李士群明明有自己的汽车、保镖,可是每次出来,都神神鬼鬼的,来回都是一人,既不带车又不带人。开始,汪曼云对李士群这招解不开,后来才知道,李士群警惕性很高,也有长期从事特务工作的经验。他怕来去带车带人目标大、遭到重庆方面暗杀。他那幢在大西路67号的花园洋房里的汽车从来不用。汽车就摆在车库里,车库门早晚都开着,摆出一副迷魂阵,让图谋暗杀他的杀手摸不清他的行踪……
其实,李士群对汪曼云也有所图。李士群虽然算是投靠了日本人,但不要说开展工作,连安全都没有保证。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在上海都很活跃,每天都有噩耗传来,令李士群一夕数惊。李士群是中统出身,对这个特务组织的活动路数、暗杀方式都很清楚,心也不那么虚。况且,在上海的中统内,还有他的把兄弟唐惠民等可以暗中为他通风报信。但对戴笠领导的军统,他却完全摸不着底,而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同戴笠关系很好,汪曼云又是杜月笙的学生。他是期望通过汪曼云巴结上杜月笙。
天从人愿,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李士群电话约请汪曼云、章正范到他家去。一见面,李士群便义愤填膺地从抽屜里拿出一份厚厚的档案,拍在茶几上,非常气愤地对汪、章二人说:“两位仁兄,可能你们还不知道吧?张师石把杜月笙出卖了!我是知道的,老杜对张师石不错呀,这个家伙太没有良心。我是出于义愤,看不过这种卖友行径才通知你们这个事的。你们看看档案里的材料吧!”
汪曼云、张师石吃惊非可,赶紧从档案袋里抖出档案——这是一套张师石向日本方面提供的有关杜月笙情况的详细材料。从杜月笙的出身、初步发迹到后来与法租界烟赌业的关系及与上海滩黑社会人物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杨虎、陈群、徐采丞、杨志雄、杨管北等人的种种关系。档案中特别强调了杜月笙与军统头子戴笠的关系以及杜月笙留在上海一帮干将(上海沦陷后,杜月笙避往香港)的情况,如:金廷荪、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陆京士、汪曼云、王先青、吴绍澍、徐懋棠、章荣初、徐大统、万墨林等。见汪曼云、章正范神情紧张,李士群大方地说:“东西太长,你们一时也看不完,就带回家去看吧。不过,看了后,务必将原件还给我,因为我在日本人那里是签了字的。他们一旦要,我就要立刻还给他们!”汪曼云见李士群如此仗义,便大起胆子提出要求:“李先生是否可以让我将原件带去给在香港的杜先生看看,我们会尽快还给你的!”
“可以,可以!”李士群满口应允。
香港,九龙。庭院深深的杜公馆里,时年51岁,具有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诸多头衔的杜月笙,正躺在他华宅中吸烟室里的烟榻上抽着大烟。这是一间宽大舒适的中西合璧的房间,地上铺着进口波斯地毯,壁上安装着空调,室内温度适中。雕龙刻凤镶嵌着进口意大利玻璃的一排中式窗棂上,金丝绒窗帘拉得严严的,屋里光线黯淡,由他最喜欢的使女雪儿陪着。躺在烟榻上的杜月笙像吹箫似的,用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托着一只镶金嵌玉的的长嘴烟枪,很舒服地闭着眼睛。躺在他对面的雪儿用一只火捻,将他拄在长烟嘴上的烟泡点燃。
“嗤——”地一声,在杜月笙苍白的嘴唇一吮一吸间,便有烟圈缕缕升起,顿时异香满屋。看杜月笙将一袋大烟烧完,伺候他抽烟的雪儿赶紧坐起身来,伸出手,将一只砌着上等龙井的鼓肚描金弯嘴小茶壶递上去,见主人并不接。雪儿便弯下腰去,将茶壶嘴轻轻插进主人嘴里。
“咕噜、咕噜!”主人很响亮地喝了两口茶,睁开了眼睛。一双虽然凹陷却灵动有神的眼睛转了两转,很舒服地吐出一口长气——杜月笙向来身体羸弱,大烟早晚必抽,但并不上瘾,完全是为了提提精神。
这当儿,管事来在门外,隔帘向他小心翼翼报告说,汪曼云专程从上海赶来,有要事向他报告。
“啊!”杜月笙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身来,赶紧说:“请汪先生赶快进来。”
当汪曼云进来时,雪儿已将窗帘拉开,为他泡好了茶,杜月笙也坐在了沙发上。汪曼云隔几坐在了他旁边的沙发上,连茶都没有喝一口,就将张师石背主求荣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报告。
“有这等事?”杜月笙听完汪曼云的报告,一下坐直了身子,转过身来,看着汪曼云,目光陡然间得非常凌厉,伸出手来,“把你从上海带来的档案给我看看。”
汪曼云拿出一个黑皮包,“唰!”地一声拉开,拿出厚厚的一叠杜月笙的挡案,放在茶几上,将第一册捧起,递到杜月笙手上。杜月笙接过来翻开,先是有关他的情况提要,因为气愤,他那张苍白瘦削的脸,渐渐转成了紫青色,两道疏淡的眉毛微微抖动。
“嗨,长见识了,真是长见识了!”杜月笙向随伺在侧的雪儿吩咐,“你去叫王秘书来。”年方二八,长相俊俏,身材适中,穿一身素色绸缎衣裤的雪儿应声去了。很快,穿西装打领带皮鞋擦得锃亮的秘书王幼棠快步进来了。
“这些东西!”杜月笙指了指放在茶几上的三本厚厚的材料,吩咐王幼棠,“你抱了去,辛苦一些,尽快用正楷字抄一份给我。”王幼棠领命而去后,杜月笙又向汪曼云问了些上海的情况并慰勉了几句。看杜月笙精神有些不济,汪曼云适时地起身告辞。汪曼云出了杜月笙的烟屋,自有下人将他带去休息。
三天后,王幼棠将杜月笙的档案材料抄完了,将原件还给汪曼云。汪曼云回上海前,又被杜月笙找去。
“曼云,你立了一大功。”杜月笙很亲切地说,“本来我想留你在香港住些时日,但我知道,你回上海还有事,在香港心也静不下来,就不留你了。你到账房去领些钱,你想领多少领多少。替我在香港给李士群买些东西送他,要买好点,值钱的,还他的人情,就说是我送他的。”
“好的,好的。”汪曼云笑得弥勒佛似的,连连点头。他当即到账房领了好大一笔钱,去香港最繁华的轩尼诗道为李士群买了一只瑞士最新产纯金高级挂表,另有两套高级西装。他自己狠捞了一笔,那就不用说了。
汪曼云回到上海,稍事休整,立刻约李士群、章正范到大上海饭店吃饭。要的是一间雅室,有悠美的轻音乐相伴。席间,汪曼云将他从香港买的东西拿出来,送给李士群,特别说明:“这些礼物,都是杜公特意送你的!”
“太破费了。”李士群从讲究备极的包装盒里,拿起沉甸甸的瑞士挂表,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正好有个好消息先告诉两位仁兄。”李士群喜滋滋地对汪曼云、章正范说,“因为日本人牵线,日前,周佛海代表汪精卫正式请我出山,为他组织、主持特工工作。”
“都谈好了?”汪曼云、章正范问。
“都谈好了。”李士群说,“但我对周先生声明,我可以出山为汪先生主持特工,但不坐头把交椅,头把交椅我推荐丁默邨坐,老丁是周先生的湖南老乡,大家都是故人,相互了解,我这一说就准。你们二位仁兄,也望多多帮助。你们想不想见老丁?若是想见,我给你们引荐。”正在想方设法找靠山的汪曼云、章正范听这一说,喜不自禁。他们当即约定,第二天上午十时,汪、章二人到李士群家见丁默邨。汪曼云心中清楚,李士群之所以不坐汪记特工的头把交椅,并不是他说的让贤,而是资历浅、威望不够。原先,李士群与丁默邨同属国民党CC,但丁默邨职务要比他高得多。
觥筹交错间,三人间关系又深了一层。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时间,汪曼云、章正范准时去了大西路67号李士群家。门铃按响后,自然是翘嘴巴苏北人张鲁来开的门。二人刚刚上楼,李士群带着一个人笑嘻嘻地迎了上来,同二人握了手后,指着身后那位虽西装革履却瘦得烟鬼似的人介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丁默邨先生。”
“幸会,幸会!”丁默邨上前一步,主动同二人握了手,相跟着上了楼上客厅。只见客厅里正面墙壁上斜钉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上面是一幅孙中山先生遗像。看汪曼云、章正范吃惊的样子,丁默邨笑着解释:“两位仁兄,这个场面久违了吧?看着也有些吃惊?从今以后,国民政府这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不是他蒋介石在重庆可以挂,我们在上海也可以挂。因为,汪先生马上就要在上海组建起一个真正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这是日本人同意的。”
汪曼云、章正范乐道:“好呀,这是好事情。什么时候开张?”
“这下好了,我们也不愁没有饭吃了。”
李士群说:“汪先生马上就要去日本访问,他回来后,所有的‘店铺’就正式开张营业。”
就在即将出台的汪精卫特务组织机构的头子丁默邨、李士群和幕后同伙汪曼云、章正范等人弹冠相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时,上海重光堂内正在召开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
重光堂又叫六三花园,是一座日式建筑的花园洋房。从一道雕花铁栅栏围墙望进去,庭院深处,那幢主楼——乳白色的一楼一底法式建筑物几乎全被蓊郁的花木掩隐。茵茵草地上,有多株日本樱花树,花开时节,烂漫一片,绯红如云。战前,这是日本特务六三老头的私宅。他躲在这里,大搞中国情报,大玩女人……上海沦陷后,这幢华屋变成了日本侵华军大特务头子土肥原的私宅。
这天,六三花园主楼二楼正中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汪精卫坐在当中主持会议;铺着雪白桌布的椭园形长桌两边依次坐着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陈春圃、高宗武、林柏生等未来汪记国民政府的大将们。引人注目的是陈公博,在河内他因为不同意汪精卫另组中央政府拂袖而去,而今天,他却来了,而且是坐在汪精卫左首第一位,与坐在右首第一位的周佛海相对。正午灿烂阳光从落地长窗中漫进屋来,屋子里很光明。
“诸位!”身着一套高档白西服的汪精卫今天气色很好,精神也很好。他挺着胸,环视左右后,振振有词地说道:“为让和平运动尽快走入正轨,早日建立中央政府,我决定近期访日。今天需要和诸位商议的第一要事是,我们未来的首都定在哪里?请诸位发表意见。”
周佛海当即表示,定都南京。理由是:既然重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是伪的,我们的中央政府才是真的,那么非南京莫属;因为,南京本来就是中央政府所在地!
高宗武却反对。理由是:现在梁鸿志的维新政府就设在南京。在国人眼中,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是日本人刺刀保护下的一个汉奸政府小朝廷,中央政府设在那里,岂不是同梁鸿志的汉奸政府小朝廷同日而语?试想,堂堂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府设在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这成何体统?在外人眼中,这个中央政府,还是中国的吗?
大家都承认高宗武的话有理。但中央政府不设在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又能设到哪里去?到大西南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行,到日本人势力范围外的任何一个地方也都不行!扯来扯去,问题还是回到原地。既然这个中央政府非设在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那当然还是在南京最宜,虽然这有点令人尴尬,但没有办法。
汪精卫暗暗叹了口气,拍板了。
“既然大家的意见最后趋于一致,那这事就这样定了。”汪精卫正想宣布会议结束,不想被他好容易重新招致麾下并被赖以为干城的陈公博要求发言。汪精卫只好应允。
“把我所知,”陈公博满面愁云地说,“日本内阁和日本大本营对我近期组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意见很不一致。”他透露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军界、政界不同的看法后接着说,“现在,局势如此之微妙。在这个时候,汪先生去访日本,倘有差错,何以对国人?”
“公博!”汪精卫对陈公博这番很不合时宜的话大不以为然,以教训的口吻说,“请你别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泄气好不好?干什么事情不冒点风险?我这次去日本,是同日本内阁通了气的。”说着,激昂起来,提高了声音,“气可鼓而不可泄!我汪某是在为和平奔走,就是为国人牺牲也在所不惜!有什么好前怕狼后怕虎的?”他的这一番话堵住了陈公博的嘴,为了给在座的“首义之人”打打气,他当即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们的经费问题解决了,而且相当宽裕。月前,为我们服务的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先生拟了一个提案交日本内阁,今已正式通过。从本月起,由日本上海正金银行每月向我们提供300万元活动经费,这是一笔巨款。”
果然,汪精卫一说,在座的都欢呼起来。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中领取好大一笔款项。其实,日本人向他们提供的巨款,是借中国人的骨头熬中国人的油——这是历史上,中国对八国联军的赔款。历年由中国海关在税收内支付,并有严格规定,若有多余款项(俗称“关余”),存入英国人的汇丰银行。日军占领北平、上海、广州等中国大城市后,发现“关余”已有相当数额,日本军方强行将所有的“关余”转入日本正金银行。
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梅思平等人就像被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当即提出:“今后,大家都要全身心地致于和平运动了,无力顾及家庭生活,组织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我们的生活问题?”众人立即附议。梅思平的话虽然说得含蓄、委婉,但意思是很明白的,这就是摊起手来,向他们的主子汪精卫要更多的钱。
汪精卫笑了一下,话说得很幽默:“思平不愧是搞外交工作的,话说得又明白又好听。”他当即大方表示,“在座诸君都是和平运动首义人物,每人发安家费10万元。但是,以后参加和运的同志,不得援引此例。”
汪精卫“出访”日本前的重要会议,就在发钱的高潮中皆大欢喜地结束了。不过,陈公博不知哪股犟筋又犯了。会后,他又持同一个理由向汪精卫告假,说他在香港的年届八十的老母亲最近身体不好,身边需要人照顾,他得回香港尽一个儿子的孝心。汪精卫没有办法,只好让陈公博又回香港当他的寓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