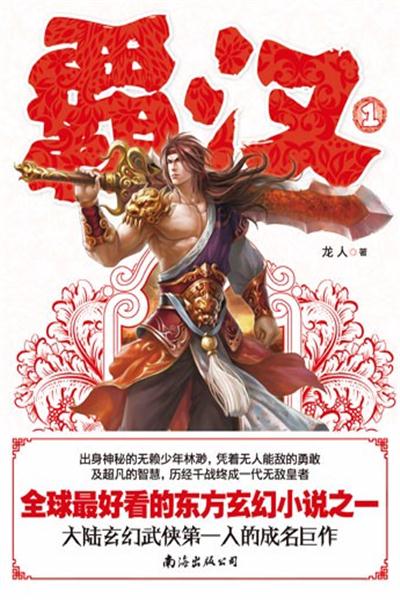凌真儿催马前行,当赶过这行人十来丈时,便勒马回头,向着轿子迎将过去。朴石安也忙勒马转头,惊奇地问道:“你想干什么?”
凌真儿没有回头,只是应道:“我去瞧瞧这位老太太的模样。”朴石安亦无奈地策马随行。
凝目向轿中望去,只见那胖妇人约摸四十来岁年纪,髻上插着一枚金叉,鬓边戴了一朵老大红绒花,一张脸盆般大的圆脸,眼细如鼠,嘴大如猪。两耳招风,鼻子扁平,似有若无,白粉涂得厚厚的,如死人一般,若不是额上流下来的汗水划出了好几道深勾,显出一道道绯红的皮肤,别人还道是具僵尸。她听到凌真儿那句话,竖起一对稀疏的黄眉,恶狠狠地瞪目而视,粗声吼道:“有什么好瞧的?”
凌真儿有心生事,对方先行起畔,她反而求之不得,勒住大白马拦在路中,笑道:“我见夫人模样长得俊,身材又苗条玲珑,便忍不住多年看了两眼!”突然一声吆喝,提起马缰,白马蓦地向轿子直冲过去。
两名轿夫大吃一惊,齐声叫道:“啊呀!”当即摔下轿杠,向一旁躲开。他们这一跑不要紧,可坐在轿子里的胖妇人就受不了啦。轿子翻倒,那胖妇人骨碌碌的从轿子滚将出来,摔在大路正中,舞手弄腿,但由于她太胖了,胖得便她再也爬不起来。凌真儿却已勒定大白马,拍手大笑。朴石安见那对胖夫妇如此作贱下人,也心中忿然,因此凌真儿作弄他们,他也在一旁看戏。
凌真儿开了这个玩笑,本想回马便走,不料那骑驴的大胖子挥起马鞭向他猛力抽来,老婆受人欺负,他平时欺人惯了,怎生忍受?便怒骂道:“哪里来的小浪蹄子!”那胖妇人横卧在地,口中更是污言秽语滔滔不绝。
凌真儿左手伸出,抓住子那胖子抽来的鞭子,顺手一扯,那大胖子登时摔下驴背。凌真儿将鞭当空一甩,并伸手抓住鞭柄,然后抖动长鞭。“啪啪”几声脆响过后,那大胖子早已鬼哭狼嚎般狂叫起来。其实,凌真儿手中的鞭子根本没有沾到他的身上。旁边那妇人见状,大叫道:“有女强盗!打死人哪!女强盗拦路抢劫啦!”无奈一旁的轿夫丫环根本就不敢过来,而路旁偶尔经过一两个路人,居然都停步围观叫好,想必是这对胖子夫妇在此一带平日作威作福惯了。
朴石安见胖妇人在一旁兀自大喊大叫,脚尖在马蹬上轻点,人已化作一道长虹落在她的跟前,仿佛天人下凡。胖妇人颤微微地抬头一看,“啊”地大叫一声,已昏在当地不醒人事了。她见到朴石安那一副奇丑面,顿时被吓坏了,倒免得朴石安动手。
这么一来,那大胖子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只以为自己的老婆是被那从天而降的丑人施了魔法,忙跪在地上直叫道:“女大王饶命!我……我有银子,女……大王饶命!”
凌真儿板起脸,喝道:“谁要你的几个臭银子?这女人是谁?”那胖子连忙应道:“是……是我夫……夫人,我……们刚从……庙里……还愿……回来。”
凌真儿道:“你们两个又壮又胖,干嘛不自己走路?好,要饶命可以,那得听我的吩咐!”那胖子磕头道:“是!是!听女大王吩咐!”
凌真儿“噗哧”一笑,但瞬即还真摆出一副“女大王”的架子,道:“两个轿夫呢?还有这个小丫环,你们三人都坐到轿子里去。”
三人不敢违拗,忙上前扶起了倒在路中心的轿子,钻了进去坐好。幸好三人身材瘦削,加起来只怕还不及那胖妇人块头大,坐在轿中并不怎么拥挤。
这三人连同和那大胖子,四双眼睛都怔怔地瞧着凌真儿,不知她有何古怪主意。
凌真儿冲朴石安神秘的一笑,不想朴石安似是知道她心中的鬼主意,他上前伸出食指在胖妇人颈上一点,那妇人顿时醒转过来。然后,朴石安抓住胖妇人的衣领,轻轻一提,胖妇人便已站起,他厉声喝道:“滚过去,听女大王的吩咐!”
胖妇人怎敢不依令而行?忙晃悠悠地跑了过去,其实她的跑跟走并没什么两样,同她的郎君站在一起,慌恐地望着凌真儿。
凌真儿抖了抖手中的鞭子,那胖子夫妇顿时吓得浑身发抖,肥肉晃动,她厉声道:“你们夫妻二人平时作威作福,仗着有几个臭钱便欺压穷人。今天遇上了本‘女大王’,要死还是要活?”
这时,那对胖夫妇早已被吓得屁滚尿流,忙齐声应道:“要活,要活,女大王饶命!”
凌真儿笑道:“好,你们两个现在去尝尝作轿夫的滋味,快!去把轿子抬起来!”
胖妇人惊恐万分,说道:“我……我只会坐轿子,不……不会抬……抬轿子。”
凌真儿面色一沉,手中长鞭一抖,顿时变为一根长棍,指着胖妇人的面门,喝道:“你不会抬轿子,本大王我可会杀人头的。”
那胖妇人只道她说杀便杀,不由大叫道:“哎唷,要死人啦,杀人了!”
凌真儿喝道:“你抬还是不抬?”那大胖子忙上前先行抬起轿杠,说道:“抬,抬,我们抬!”
那胖妇人无奈,只得上前矮身将另一端轿杠放在肩头,挺身而起。
这对胖子夫妇平时补药吃得多,身体也着实健壮,抬起轿子迈步而行,居然抬得有板有眼,丝毫不显吃力。一旁众人忙拍掌喝彩:“抬得好!”
凌真儿与朴石安骑马押在轿后,直驰出十余丈,方才双双纵马急驰,凌真儿并叫道:“你们好好抬,在镇子上本大王等着你们!”她又转身对朴石安说道:“安哥,咱们走吧!”
朴石安笑道:“是,女大王!”
两人忍不住哈哈大笑,放马疾行。不知翻过多少道山岗,越过了多少架桥梁,依然没有看到有集镇。朴、凌二人未带干粮,由早晨到现在他们未进一口食物,早已饿得肚皮贴着背了。幸亏二人所骑的马均是上等好马,一路疾行如飞,坐在马背上亦丝毫不觉得累。
奔行了一个多时辰,不知不觉已驰行了百余里。总算到了一个集市,不过他们已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了,估计已进入河南境内了。
这个集镇人烟稠密,市肆繁盛,他们差点以为这便是南阳城了。不过,管他是什么地方,先找一家酒楼解决温饱问题再说了。
朴、凌二人来到一家酒店的门口,酒店里冒出的香味熏得他们难受至极,忙把马匹的缰绳系在店门前的马桩上。早已有店小二出来招呼,见他们衣着华贵,招待得特别热情。二人进店入座,随便要了几盘饮菜,近乎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吃得差不多了时,朴石安方吩咐店吩咐上几壶酒,不消多时,店伙计已端上三壶汾酒。
朴石安揭开泥封,顿时一股清香荡入心腑,他哪里还按捺的住性子,仰起脖子就着壶口“咕噜”地灌了进来。一口气下去,一壶酒已点滴不剩进入了他的肚子,然后大叫道:“好酒!杏花村的汾酒果然名不虚传!”
一旁的店小二面有得意的说道:“公子爷好眼光,这正是小店特地从山西杏花村购来的一批上好‘涡头汾酒’。小的见公子爷气度不凡,一定品味不俗,因此便端了上来,果真如此,公子爷一喝便知是汾酒!”
“咕噜!”一声,朴石安又喝了一大口酒,大笑起来,凌真儿知其好酒,早已见多不怪,兀自吃着饭食。
这时,从店外走进一个衣衫褴褛的落魄书生,右手摇着一柄破旧折扇,左手却提着一个朱红大酒葫芦。他吼道:“呸!这等小酒家也能有什么好酒?只有那些俗人方称之为好酒,可怜!可悲!可叹!”
店伙计见是一个穷酸秀才,顿时脸色一沉,上前拦住,喝道:“哪里来的穷小子,跑到这儿来撒野!滚,出去!”
朴石安看不惯店伙计那见钱眼开的小人形态,更为那穷秀才的“不凡”言语所动,便走上前隔开了店伙计,抱拳对那穷秀才道:“兄台如若不弃,在下愿与兄台共品美酒。”
那穷秀才冲着伙计白了一眼,道:“真是狗眼看人低,还怕我付不起帐?哼!就是把你这整间酒楼的酒都拿上来,我闻都懒得去闻。”
朴石安忙接口道:“兄台何必和这等人过意不去?来,请到在下这边一坐。”
店伙计见是朴石安出面,也没再说什么,悻悻地望了那穷酸秀才一眼,便退了下去。
朴石安让店伙计重新上菜,凌真儿在一旁正要为他们二人斟酒时,不料那酸秀才却摇手道:“姑娘且慢,这等汾酒如何能下肚,晚生虽然与这位兄台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因此必须喝上等好酒,以示庆祝。”
凌真儿闻言便欲唤店伙计。
那秀才又道:“这等小店哪有美什么酒。来!晚生请兄台尝尝这葫芦里的酒。”说罢他拿起朱红大葫芦,拔开塞子,顿时酒香四溢。
朴石安一闻便知是几十年陈酿的梨花酒,忙抱拳道:“这是兄台珍藏六十年的梨花酒,在下岂敢糟蹋此等美酒?”
那秀才一怔,复又大笑道:“不错,兄台一闻酒气,便知这是藏了六十年的梨花酒,果真乃酒中君子。晚生姓甘,单名一个鼎字。敢问兄台尊姓大名?”
朴石安道:“在下姓朴,双名石安。”
甘鼎道:“酒逢知己千杯少!朴兄,来!咱们痛饮几杯,切莫推辞!”他居然不识得在江湖中声势显赫之推浪帮帮主朴石安的大名?当真不是江湖中人!
朴石安也是性情中人,当下大笑道:“那在下就不客气了,小二!拿杯子来。”
甘鼎见状,却道:“非也,朴兄有所不知,你对酒具如此马虎,于饮酒之道,显是未明其中三味。饮酒须得讲究酒具,喝什么酒,便用什么酒杯。”
朴、凌二人闻言怔了一下,朴石安忙道:“还请甘兄赐教。”
甘鼎亦不谦让,指着桌上所剩下的一壶汾酒道:“喝汾酒当用玉杯,唐代李白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朴石安不禁连连点头称是,心中对这长着一个硕大酒糟鼻的甘鼎极为称叹,连一向不喜饮酒的凌真儿也听得心动神往。
只听甘鼎又道:“喝葡萄酒当用夜光杯。古人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我辈须眉男儿饮之,未免豪气不足。不过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后,酒色如同血色,饮酒有如饮血。又有诗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快哉?”
这时,店小二已以来两只瓷杯,听到甘鼎的这一番见解,不禁怔立当场,对这甘鼎也是另眼相看。
甘鼎拍了拍那酒葫芦道:“至于这梨花酒,则应用翡翠。亦有古诗云:‘红袖织绫夸拂叶,青旗沽酒趁梨花’。”
店小二忍不住插口问道:“那饮高梁酒,用什么杯子呢?”
甘鼎白了他一眼,不过还是说道:“饮高梁酒须用青铜酒爵,方才有古意。”
凌真儿也笑着问道:“小女子也请问先生,若饮绍兴女儿红,应用什么酒杯?”甘鼎答道:“须用古瓷杯。”凌真儿又道:“旅途之中,又哪来这么多珍贵的酒具呢?”甘鼎笑道:“善饮酒之人若身边无佳器,遇有美酒岂不糟蹋?”
一句话没说完,只见甘鼎伸手入怀,掏出一只酒杯来,光润柔和,竟是一只羊脂白玉杯。众人俱惊,瞪大眼睛望着甘鼎,只见他不断从怀中取出酒杯,有青铜爵、夜光杯、古瓷杯、琉璃杯、翡翠杯、象牙杯、紫檀杯、牛皮杯、金杯、银杯、石杯,当真应有尽有,难怪他总挺着大肚子。那店伙计更是万万没有料到,这穷酸秀才的怀里,竟会藏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酒杯,先前确实是有眼不识真金。这么多的杯子,若有一只属于自己,那也可以换得几两银,够自己用上几个月了。
甘鼎只将那个翡翠杯留在桌面上,其余均收入怀中,然后将葫芦中的梨花酒倒入翡翠杯中。向朴石安道:“朴兄,请干了这杯酒。”
朴石安朗声应道:“好!”便端起酒杯欲饮,凌真儿见状忙道:“安哥!”她是怕酒中有毒,朴石安自是明白她的意思,但他却摇了摇手道:“真儿,不必担心!”说罢,他已仰头饮尽杯中之酒。
“果真好酒,味道甘美醇厚,回味无穷,妙!妙!”朴石安饮完酒后连声叫好。
甘鼎见状笑道:“朴兄好酒量,我这梨花酒一般人沾唇即醉,而你居然喝了一杯仍兀自不倒,钦佩钦佩!但我更佩服朴兄的胆量,朴帮主,你枉为一帮之主,今日中了我的奇花散你焉有命在?”原来他早已知朴石安的身份,说话间,他不时地瞧着凌真儿。
凌真儿闻言果然大怒,拔剑而起,喝道:“大胆贼子,竟在酒中下毒,快把解药拿出来!否则小心项上人头!”
谁知,朴石安中了毒,居然笑道:“真儿,我怎么会中毒呢?”凌真儿大为惊骇,疑惑地望着他,手中的剑依然指着甘鼎。朴石安这才向着甘鼎笑道:“天下若有如此味美的毒药,朴某倒愿不要这条命也要喝上一顿。”
突然,朴石安趋前向甘鼎跪下,施礼道:“晚辈叩谢前辈之恩!”他这一举动令凌真儿、甘鼎均为之一愣。
甘鼎恍然道:“好你个臭小子,原来你早就知道我老人家……哎呀,不好玩,我去也!”说罢,他已如一阵清风飘出了酒店。
朴石安笑着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灞更为之不解,茫然地问道:“安哥,那甘鼎的声音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苍老?他是谁呀?你怎么又向他下跪呢?”她满肚子的都是疑问,因为太迷惑了,所以只好一古脑儿地说出来请教朴石安了。
朴石安却笑嘻嘻地对她道:“等会儿再告诉你。”他唤来店伙计,付了帐,便同凌真儿一起走出酒楼,牵了马匹便认准方向往南阳策马而去。凌真儿虽有满腹的疑问,但朴石安不说,她也没有法子,只好一路死缠着他问。
一晃眼,二人已驰出了十来里路,朴石安策马上了一个土岗,四下张望一下,叹道:“可惜!”凌真儿忍不住又问道:“安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快告诉真儿,好不好?”她这回用起了媚态,看来她心里真是急不可奈。
不过,她这一招确实百试不爽,朴石安立马投降,道:“刚才那人是‘百变酒丐’风老前辈,他给我喝的酒其实是件宝物,喝一口便可增长三年功力,而我喝了满满一杯,起码可以增长十年以上的功力,你说我该不该谢谢他老人家?只是我何德何能,再次受他老人家如此大的恩典,真是有些心中有愧!”
凌真儿瞪大眼睛望着朴石安,已极为兴奋,她叫道:“真是他?”她这么大声叫喊,把经过他们身边的一个樵夫给吓得一颤,并马上背着一捆柴加快了步伐。
凌真儿并没在意,接着道:“我听爹说过,风老前辈行侠江湖时,最好饮酒,又善于易容,还说他是丐帮的上代帮主,所以江湖中人都称他为‘百变酒丐’。哇,安哥,你真幸运哩!不过,我倒没听说过他老人家酒葫芦里的酒喝了可以增长功力这回事。”说罢,她又望着朴石安,希望他述出答案。
朴石安本想卖一下关子,但一看到她那急切的目光,心觉不忍,便说道:“风老前辈与我师父是生死至交。我师父像我这么大年龄时也是遇上了他老人家,他们都好酒,借酒相交,于是结为朋友。”
凌真儿道:“那你师父不也喝了那药酒,增长功力了?”
朴石安叹了一口气,道:“若真如此,师父他老人家也不会英年早逝。风老前辈葫芦里装的药酒可能是最近几年才酿出来的,其实这么多年来,师父和我都没想到可以借助奇丹妙药来增长功力,否则便不必去练那武羊奇书了。同时也使我终于明白了,说不定我身上这本武羊奇书是真的,只是练到一定的时候要借助外力才行。对,一定是这样的,哈哈……真儿,我的功力是可以增长的!”激动兴奋之余,他居然伸手抱住了凌真儿。他们是并驾齐驱,两马间隔甚小,朴石安将的手臂一伸便可揽住凌真儿。直到温玉满怀,他才惊觉自己居然——如此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