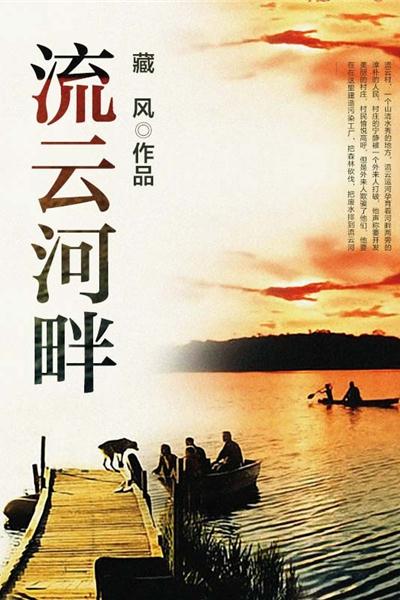那晚,李叶茴讲了整整四个小时“北京户口”的故事。张庭园一句话都没接。他拥住了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李叶茴身体绷直,一动也不敢动。她听到张庭园均匀的呼吸声。他睡着了。
回忆起悲伤过往,李叶茴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那些极力想忘记的脸一股脑全回到记忆里,那些被李叶茴在心里敲碎的镜头竟然团结起来、凝结成一部完整的童年悲剧,开始循环播放。
李叶茴以为自己已然在心里建立起积极自信的“上层建筑”,却发现那些还未释怀的故事、还为未和解的人们才是自己人生的地基。
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张庭园的叩门声准时响起,进来后,他顺理成章地躺在李叶茴的床铺上:“想睡里面还是睡外面?”
“里面。”
于是张庭园挪到外面,但是将靠里的手臂摊开。
他们随便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问一下彼此是否开心。他们心知肚明,彼此都不开心。
第三天、第四天也都是如此,只是张庭园不再询问便主动躺到外侧,然后李叶茴也会很上道地直接倒在他身边。她请求张庭园贴着她的耳朵唱歌,任由他那略带沙哑的温柔嗓音久久地回荡在梦里。
张庭园成了李叶茴现实生活的“神秘伴侣”,这却是李叶茴最不想成为的关系。
李叶茴习惯了张庭园的拜访,习惯到不再去纳闷双方的关系、习惯到如果张庭园没来,她就睡不着、习惯到拒绝和朋友去自习室,以便把夜间的档期留给不速之客。
每次张庭园离开,偌大的房间就只剩下干巴巴的阳光、她的内心也迅速被晒干。李叶茴不敢赶他走,更不舍得赶他走。
她只得安慰自己:神秘来宾会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与众不同。而她自己,不是做梦都想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吗?
李叶茴千方百计让自己对他挑剔,可是张庭园这个有些残缺躯体的人,在她心中不可控制地完美起来。
还好,梦想可以拯救她。每天醒来,李叶茴都毫不犹豫地从张庭园的怀里挣脱,借此来表示对儿女情长的嗤之以鼻。她在桌边奋笔疾书,却又忍不住回望张庭园熟睡的脸庞。有很多次,她趁他没醒,再次偷偷钻入他的怀抱,却从不敢久待,好像自己还未沦陷。
即便不可抑制地产生依赖,李叶茴不得不承认,她逐渐发现张庭园并不是她想象中的“天之骄子”。他的呼噜声不到中午不会停止,晚上也是做完乐队的活动才来打扰李叶茴。仔细算算,他每天要花七八个小时在杂七杂八的事情上。
李叶茴很困惑:“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乐队上呢?不是说要好好学习、毕业后带自己的创业团队有所作为吗?”李叶茴让语气轻松自然,充满好奇,生怕对方看穿自己的质疑。
“哦,因为大学怎么上是个人选择。我在做喜欢的事情,放弃什么都是自愿的。不过带领乐队、组织团队都对我的软实力提高很大啊。”对方轻描淡写。
李叶茴对此嗤之以鼻。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搞那么多花花肠子又没用。
不过李叶茴为了完成表格上的二三十项任务,也忙得焦头烂额。辩论训练间隙,她会敲敲代码、假装做笔记;而上课时,她会思考即将到来的辩论赛的讨论框架。三心二意的结果就是两者都无法全情投入、均表现平庸。可是她依旧坚信“勤奋是解药”,成魔般地将每一秒都投入奋斗、彻底失去享受生活的能力。
直到三四年后,李叶茴才能理解张庭园所说的“个人选择”。最初的最初,大家都在扮演“精英”、因为大人写好了剧本。后来,一些人演着自己的剧本、假戏真做;一些人还跟着社会的编剧越演越失真,最后做了观众。
李叶茴成功了,她讨厌了他,但是也爱上了他。那些李叶茴留意他的所有行为,期待透露着爱意的蛛丝马迹;但是若真的被爱上了,李叶茴敢接受吗?母亲会被美丽的歌声打动、从而忽略那消失的手臂吗?当然不会,李叶茴甚至听得到李斌的冷嘲热讽:“你难道想掩饰自己的肥胖、所以找了一个永远不可能抱起你的男人吗?”
不过她日夜观察的“蛛丝马迹”很快告诉她:张庭园没爱上她,更没想表白。
比如张庭园的双手常常下滑、唱歌的双唇也会在脖颈游走;比如李叶茴试探着问:“明天去你的房间吧?”张庭园会瞬间拒绝,理由是:“我房间门口总是有熟人,不想被撞到。”
这是个好契机去说服自己死心,但她远没有自己所想的理智。
Raffles Hall有很多中国人,可能因为它靠近工程系 -- 一个被中国人占据了的大系。在十月一号中国国庆节来临之时,Raffles Hall内学生会都会找几个小有才华的居民,凑个“爱国晚会”。李叶茴也被滥竽充数,安排了一个小提琴独奏:《金蛇狂舞》。
可是她已经三年没碰琴了。
左右为难时,有个人突然嚷嚷起来:“张庭园,你不是吹长笛,你们合奏一个?”
张庭园正和乐队漂亮的女孩子们在大厅另一角说说笑笑。猛地听到自己的名字,他不耐烦地回应:“什么?和谁合奏?”
“和李叶茴。认不认得?来,叶茴你站起来。”
李叶茴克服尴尬,向远处的张庭园挥挥手。
“哦,你好。”他也仿佛真的从未相识般地跟李叶茴挥手致意。
“她说好久没有碰小提琴了,你个长笛高手,来带带她?”
张庭园面露难色:“我已经有两个节目了……”
大家劝他:“你音乐玩得那么好,带带别人岂不是举手之劳。”
李叶茴挤出八颗牙齿、眼睛却没眯起来:“没关系,我想挑战独奏。都是自己人,拉得不好还请大家多见谅了。”
人们又开始讨论下一个节目。李叶茴回头张望,发现张庭园早就又投入和朋友嬉笑打闹中了,一脸的如释重负。
那晚,张庭园又来了,两个人对于白天的尴尬只字未提。
可即便没有白天产生的隔阂,此时的他们也已然是两块枯竭的土地、除了旧饭新炒彼此悲惨的成长经历、说那些毫无交集的生活琐事,就再也挤不出共同话题了。
张庭园为了延缓尴尬唱着歌,李叶茴不得不违心地承认,其实他们都无法共享当下、更不要妄想什么未来。
……
他们之间甚至连朋友也不是。更可怕的是,他们关系的决定权完全在张庭园手上。
李叶茴的懦弱已经严重到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地步。如果不是第二天早上的另一件事情,她可能真的会把自己交给张庭园。
一直以来,李叶茴都刻意避免太过参与他的私人生活,毕竟在黑夜酝酿的关系,应该和光天化日下的世界有着清晰界限。但那天早上,她就像没有安全感的“女朋友”一样,忍不住好奇地翻开了张庭园的手机。那密码她早已在黑夜中偷窥多次、烂熟于心。
她安慰自己,这不是搜查,只是好奇。
置顶的消息来自于“第二个穆洛娃”。穆洛娃是名扬全球的小提琴女神。
第二个穆洛娃: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吧。我害怕。
张庭园:害怕什么?不见面我怎么帮你排练节目?
第二个穆洛娃:这样不好。
张庭园:不要想太多,顺其自然,好吗?
然后是五分钟的空白。
张庭园追问:可是我想见你。
然后是二十分钟的空白。
张庭园又问:你在哪里?我给你唱歌。
“第二个穆洛娃”再也没回复过。时间过了一天。
张庭园:我刚刚看到你在超市,穿着运动装,要去运动吗?
第二个穆洛娃:嗯,去跑步。
张庭园:我陪你?
第二个穆洛娃:随便你。
前一天的张庭园确实没来找她,原来赴别人的约。
李叶茴想起自己和他的聊天记录:
张庭园:在吗?
李叶茴:在。
然后张庭园就会直接过来,自动躺在床铺上……多酷啊,毫不拖泥带水。
李叶茴,你真是太贱了!
李叶茴觉得自己的生活无比恶心,也觉得自己的过去无比恶心。和那些被人追捧、受尽宠爱的小公主相比,自己算是什么?就算现在瘦了、漂亮了、能到所谓名牌大学求学了,可是卑微和缺爱依旧是深入骨髓、可以主宰命运的。
第二天晚上,李叶茴没有回房间。她知道张庭园在门口敲了门,也试图扭了门把手,也知道他一脸疑惑地掏出手机发短信给自己:“在吗?”
李叶茴没有回复。张庭园再也没有询问。本该疯狂的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度过了。
接下来的一周,李叶茴再也没回过张庭园的“在吗?”,也逼着自己在自习室待到凌晨。
可是自那之后,李叶茴病了。
非常非常多的病。
第一症,相思。
没了张庭园的夜晚,孤独排山倒海。她偶尔后悔自己的狠心,而这后悔本身透露的“不知羞耻”让她更加自卑。李叶茴开始幻听。她总会在即将入睡前听到轻轻的叩门声,但是猫眼外却是沉默的红砖墙。张庭园的朋友圈成了李叶茴的极乐园,好像他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句感慨都是为她而拍、为她而写。
第二症,失眠。
这是老朋友了。她怕错过张庭园的敲门声,养成了竖起耳朵、头朝门睡的习惯。心脏也一分为二:一半回忆,一半等待。这么久,失眠症终于击垮她:听课困难、成绩下滑、为了追赶课程,她没有时间去社交、朋友也被她身上的负能量吓走。
然而,在这个精英遍布的地方,“堕落”不是一个人的事。当自己陷入死循环,而曾经同起点的他们无论是学习还是社团,都做得顺风顺水,李叶茴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属于这个地方。她恍然大悟:我是靠演技进来的,而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精英!这样想她才舒服多了。
最后一症,偷窃。
一开始,她只是爱上了暴饮暴食。享受着食物带来的“瞬间快感”,李叶茴就像在吸毒者的天堂。可是新加坡的食物太贵了,勤俭节约的她只能忍耐。
各方面的失利汹涌而来、在李叶茴的心里砸下一个大大的缺口,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免费”的美食在冰箱发光……“贫穷”再也无法制约她、那么道德呢?李叶茴发现自己如此道貌岸然。她被全身的渴望冲击着、开始胡吃海塞。
这不是贪婪,这是病。李叶茴总是不记得是什么驱动她这在阴森的厨房、像狗一样蹲在寒气四冒的冰箱前、嘴里“吧唧吧唧”地嚼着别人的食物,毫无羞耻之心。
曾经是个不自律的胖姑娘,至少还能违心地夸自己可爱。可是现在,她是个坏姑娘、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一个为了食欲放弃人性的野兽。
人们对小偷从不宽容,冰箱门上贴上了“小偷去死”之类的便条。李叶茴躲避着厨房的月色,睁大眼睛仔细辨认那些恶毒的文字……她没资格嫌他们恶毒,这是她应该承受的。被那些咒骂一勺勺地挖走尊严,李叶茴觉得心痛,但是痛的背后是快乐。最痒的那块肉被狠狠挠了一下的快乐。
直到有一天,被失眠摧毁皮肤、被饕餮摧毁身材、被贪婪摧毁人性的李叶茴、在厨房作案时,被自己日思夜想的情郎张庭园看到了。
哦,原来这就是那个这个Raffles Hall都在骂的“厨房大盗”啊。
那一瞬间,李叶茴被闪电劈击中了,不仅心脏即将爆炸、肉体也感到切切实实的疼痛。
张庭园看着她、又像没看着她。李叶茴倒是在他的嘴角看到一丝嘲笑……或者怜悯。啊,那朝思暮想的双唇啊,只可惜此生再也看不到那八颗洁白的小牙了吧。
张庭园走了,寻着月光的轨迹。李叶茴双手颤抖了好一会才咽下含了半天的面包,或者意大利面,或者别的什么。李叶茴远远地躲开冰冷的月光,回到了冰冷的宿舍。
张庭园再也没有敲过她的门。来自两个世界的流星终于擦肩而过、渐行渐远。神秘伴侣的游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