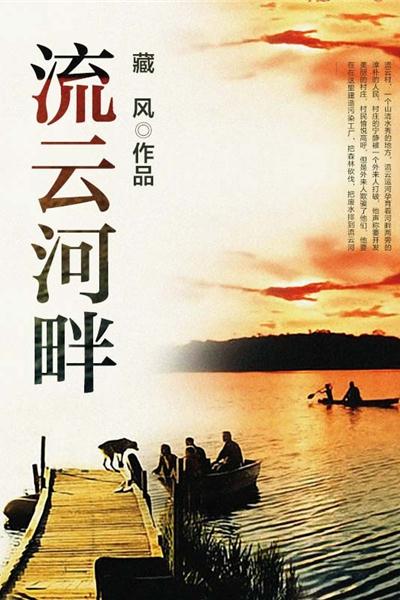这是位于黑龙江江畔的一座小城。小城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小兴安岭;小城南面,是遍地沼泽的三江平原;小城北面,是咆哮奔腾的黑龙江……历史上,这里曾是辽金重地,奥里米古城历经千年,仍在诉说着那段兴亡。但是,当后金执掌江山时,这里和整个东北一样,被封禁起来,成为一片荒野,直至大清倒台,方有人在此开矿。1934年,日本人在这里成立了满洲炭矿株式会社,1939年,伪满国进行机构改革,将附近的汤原、萝北两县析置榷立县,使这里成为一座著名的煤城……这里,就是我要投奔的鹤岗。
当天夜里,我顶着暴雨,在黑暗的伊通河漂到天亮,看到眼前的水面越来越宽,我知道进入了松花江了,我在松花江上漂到黄昏,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座大都市,这才弃船上岸……没想到,这里正是哈尔滨。我在哈尔滨待了两天,最后,和一大群逃荒的人挤上一列火车,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方始来到了我的目的地——鹤岗。
我知道,我已经逃出来了,但对眼前出现的这座都市,并没有长出一口气的感觉,对未卜的命运,似乎更加忐忑不安。这也许是小城给我的暗示。小城太灰暗了,似乎是从煤堆里扒出来的一样。一座座和式见方见角的房子,全都挂着黑黑的煤灰,那煤灰从房顶从墙面,延伸铺展到街道上,每当一辆汽车经过,就像冲过一头怪兽似的,挟裹起漫天黑灰……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钻进黑灰中,按父亲给我信封上的地址,见人就打听,去找住在南山矿的表姐家。
多年前,父亲的二姨,在吉林四平街诞下一帮儿女,儿女们再次繁延,大女儿嫁给一户姓朱的人家,头胎生下一个姑娘,姑娘长大后嫁到鹤岗,这就是我要找的表姐——朱春花。表姐结婚时,曾带她丈夫来看过我父亲。表姐的丈夫叫李国林,是个粉匠。李国林看我父亲养了那么多猪,很是喜欢,说鹤岗是工业区,猪崽不好买,否则,他家粉坊的下脚料,就不用扔了,也能养猪了。父亲听后,挑了一公一母两头健硕的猪崽,送给了李国林。李国林回去一段时间后给父亲来过一封信,感谢父亲送他的那两头种猪,让他家繁殖了一大群猪。
这些事儿,母亲讲过,但我并未留意,甚至对这位表姐和表姐夫,脑海中也没有什么印象。表姐真像父亲说的,见到信就会收留我么?或者,这么些年了,她家有没有搬走,搬走了我又怎么办?
我没有一点把握。
一路打听,我找到了南山矿。所谓南山矿,就是一片破败的贫民区。一座座房子大小不一,长短不齐,房挨房,房挤房,散乱无章地堆在这片肮脏的山坡上。同样,这里的煤灰更多,脏乱的街道上,煤灰铺有两三寸厚,踩上去,正应了一句东北土话,暴土扬场的。这样的地方,似乎并不影响人们的生活,煤灰里,也长出了瓜果蔬菜,很多豆角蔓上虽然挂着一层厚厚的黑灰,居然也开花结角了……更奇怪的是,这样大的煤灰,一些人似乎有意要突出自己的亮色似的,很多妇女穿得大红大绿,弄一张小板凳坐在门前,在黑灰中展览着自己。这些妇女,或纳着鞋底,或织着毛衣,或摘着菜帮,眼睛不时地打量着路人,让人想到蒲松龄在《婴宁》里的描写的“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那句话,但这些“个儿郎”都是女的。我向一位“目灼灼似贼”的妇女打听李国林家,这位妇女很热情,热情到有些过份,说:“打听他家干啥呀?上我家得了。”从她挑逗的眼神中,我明白这种热情并非善意,赶紧头也不抬地离开了。后来听表姐说,解放时,哈尔滨、佳木斯一些妓女,不少都发配到了这里,嫁给了煤黑子。有些妇女在家中无事可干,又开始重操旧业……我在街边看到的这些妇女,当属此类。
我在逼仄狭窄的街道里左转右绕,问了一些人,都没有找到表姐家,后来,绕上大道,见远处一个瘦弱的女人拎着一包东西,正向我走来。女人穿得很朴素,感觉和那些花红柳绿的妇女不是一类,这才壮了壮胆子,向她打听,没想到,打听对了,走来的妇女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表姐朱春花。
表姐三十多岁,长得很瘦小,显得很干练,一双大眼睛,总在眨来眨去,好像特别有主意似的。表姐听我是牛家坨子张万山的儿子,夸张地看着我,说没想到,她离家时,我才这么高,现在成了一个大小伙子。她比比划划地讲着,将我领到一处不大的平房前,告诉我,这就是她的家。
表姐推开门,马上咋呼开了,对屋内一个男人说,你看谁来了?
这个男人,一定就是表姐夫李国林了。
表姐夫处处突出一个“大”字,大个子大头大脸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大屁股,两只大手,足有蒲扇大小。不知道他用这两只大手,拍打出多少粉条?不过,表姐夫也有缺点,有鼻炎,鼻下经常挂着鼻水,如此,堵塞了鼻孔影响了说话的声音,一说话,带有囔哧囔哧的共鸣声。表姐和表姐夫还有一个儿子,叫大宝。大宝深得乃父遗传,长得虎头虎脑,才八岁就像个半大小子了,十分招人稀罕。
表姐夫和表姐一样,对我很热情。听我是张万山的儿子,马上提起我父亲给她的那两头小猪。那是两头民猪,正宗的东北本地猪,“民”就是长得慢的意思,这种猪虽然长得慢,却忍饥抗寒、耐粗饲,大的能长到千斤重……表姐夫说:“那头母猪才添和人呢,每窝都下十几头猪崽,要不是合作化,我家他妈的早都有了养猪场。”
表姐夫介绍完猪,表姐插嘴讲起表姐夫的家世。表姐夫家开粉坊是世袭的,从他爷爷那一代便在鹤岗开粉坊,后来传到他父亲又传到他,合作化后,他家的粉坊被没收了,但表姐夫还在干本行,给公家漏粉。表姐介绍完粉坊,又抱怨她家的房子,说“原先,我们就住在粉坊里,那房子才大呢,这一归公,将我们赶了出来,才住在现在这么小的地方。”
表姐家的房子确实不大,三十多平方,中间用木板隔成了里外屋。外屋十平米是厨房,里屋是卧室,一铺大炕占去了一半儿。我的到来,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表姐指挥表姐夫,把大屋靠近窗子的两个木箱移到厨房,用木板搭了一张临时木床,也就是我的床铺了。大宝感到新奇,在床上翻身打滚儿。
晚间,表姐做了好几个菜,张罗着我和表姐夫喝酒。我是第二次喝酒,有第一次和老师喝酒的教训,没敢多喝。
说到此行目的,我没敢说是逃出来的,只是说家乡人都入社了,学生天天干活儿,我父亲想让我托表姐夫,在鹤岗给找个事儿干,哪怕下井也行。
表姐夫当即反对,说:“下井是挣得多一点儿,但那哪是你能干的?要找活你就放心吧,有表姐夫在,不愁没活干。”
表姐在旁表扬表姐夫:“守义,你不用担心了。别看你表姐夫是漏粉条的,看着不起眼儿,这活儿那才交人呢。整个鹤岗,谁不高看你表姐夫一眼。”
我们唠到很晚才睡去。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都起来了,简单吃完早饭,大宝上学去了,表姐夫和表姐也去上班了。表姐也在粉条厂上班。家中只留下我来看家。
一个人静下来,百无聊赖,寂寞、空虚、孤独像张大网般罩住了我,让我茫然无绪。我又重新躺在厨房里的床上,望着水缸酸菜缸油乎乎的灶台,望着一群苍蝇嗡嗡飞着,脑海里跳来跳去的却是学校里的一切……这些人,一个个就像都把脑袋挤在一个万花筒里,不时变幻着模样,一会儿是校长王大胖子,一会儿是工作组头头,一会儿是吊在校门上的老师,一会儿是和我一起出逃的谭宾,一会儿是牛淑芬、钟玉花……当然,还有我的父母,父亲那一脸的坚毅,母亲那抹泪的样子,最后,又定格在父亲站在河岸上注视我的身影……我当时虽然看不见,但我知道,父亲一定在夜色里站了很久很久,他的目光透过黑暗,透过风雨,注视着我如何来漂完全程,甚至是漂完我人生的全程……想到父亲,我又想到了我自己,经历了这场变故主,我还有未来么?但我还是想有未来,而未来,现在也只能靠表姐夫了。
我来到表姐家一待就半个月了,表姐夫一直没有帮我找到工作。
每一天,我都在表姐家中待着,表姐不让我出去,说南山矿这地方乱,不但有我看到的那些妇女,还有解放时很多胡子都藏在了这里,别看平时静悄悄的,说不准哪里就钻出一伙人,将人整死扔到矿井里……这地方这么乱?我也就只好耐心等待了。
表姐和表姐夫配合默契。表姐夫找不到工作,表姐不怨他,只是安慰我,说快了,让我不要着急。但我不能不面对现实,1959年的夏天,吃野菜、树皮、草根的现象已经波及到了全国,表姐全家吃供应粮,三口人口粮九十斤,但在缺少副食的情况下,这些粮食填饱他们自己的肚子都难,何况又加上我这么个大小伙子。好在表姐表姐夫在粉条厂上班,近水楼台,每天都能往回拿些土豆或凉粉,既当菜也当饭了。
我天天数着日子,第十八天头上,表姐夫一下班就囔哧着鼻子喊:“妥啦,守义。你小子有运气。又上学,又挣钱,又教学。表姐夫给你全办明白了,这回就看你小子的本事了。”
表姐夫云山雾罩的,半天我也没弄听明白。表姐看我愣在那儿,解释说:“矿务局耿科长爱吃凉粉,经常买。你表姐夫求她帮你找工作,她今天来说,矿务局要招收五十名教师,但要考试和培训,培训三年,培训时发工资,毕业后安排在矿区学校教学。不知你有没有把握考上?如果觉得行,明天上午去教育科找耿科长填表。”
听完表姐的话,我十分高兴,说道:“行,肯定能行。我会考上的。”
第二天早晨八点,我找到矿务局教育科,来到耿科长办公室。
表姐讲的耿科长是个女人,二十七八岁,皮肤白嫩,眼睛清澈,长得很漂亮。耿科长听完我的来意,态度和蔼地问我:“听李师傅说你还在上学,你愿意在教育事业上干么?”
“愿意。”
“你多大了?”
“我十八了。”
耿科长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又松开了,若有所思地说:“嗯,你是来报名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对了,还有一个女孩叫谢玲,也和你同岁。就破例收下你俩吧。”她递给我两张表格,说道:“回去把这两张表格填好,明天给我送来。好好准备功课,后天来教育科考试。”
我高兴地离开了耿科长。往回走的路上,我猜想会考什么样的试题,难度大不大?令人奇怪的是,脑海中老是浮现耿科长的影子,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爱吃表姐夫漏的粉条呢?
考题都是初中课程,很简单,我答得很满意,考的分数也高,被矿务局录取了。让我意外的是,宣布录取名额时,耿科长把录取通知书交到我们手上,还宣布了一个更好的消息,说,矿务局体谅我们,怕我们有困难,当天就给我们发放粮票和伙食费。伙食费三十六元五角,粮票三十二斤,以后这就是我们每月的标准了。
我把钱和粮票揣进兜里时,心里乐开了花,立刻精神了。因祸得福,我也能挣钱了。
这时,耿科长说的那个女孩谢玲,满面含笑地走了过来。这是一个会笑的女孩,弯弯的眼睛不笑也像笑,笑起来,两个深深的小酒窝溢满笑容,感觉随时都会溅出来。谢玲大人似的自我介绍:“张守义同学,你好,我叫谢玲。认识一下好么?”她边说边伸过白嫩细腻的小手,我握住她的手,心里一阵狂跳。从耿科长说过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开始,我就留意她了。考场上,我们隔着两排,斜对角坐着。耿科长点她名字时,我注意看了看她,当时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谢玲长得太好看了。我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居然主动将手伸给了我?我正在想入非非时,一低头,发现她的手我仍然握着呢,不由面红过耳,慌乱地说:“你……你好,对……对不起,把你握疼了吧?”
谢玲好像没什么感觉,满面含笑地看着我,老朋友一样问道:“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我经常走神儿,请你原谅。对了,你对市里熟悉不?我想请你当向导,买点东西。”
谢玲爽快地答应了。
我想给囔哧鼻子表姐夫买两瓶酒,给大宝买一斤糖果。谢玲陪我走了几家食品商店,但是,就是这两样最平常的东西,却让我们费尽周折,所有商店一个口径,扔来句“凭票供应”就完了。
我感到失望,诺大一座城市竞然买不到两瓶酒。
谢玲鼓励我:“没关系,一定能买到,我们往城边走走。”
我们走到城边一家叫新曙光的食品商店,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新曙光商店,曙光并不多,店内黑乎乎的。两个女服务员站着闲聊,一个老头坐着打瞌睡,三五个闲人聚在柜台外,东拉西扯着,不过是找个地方放放屁股。商店里显得冷清、空旷。谢玲让我在一旁等她,说,这回看她的。谢玲径直走到卖酒柜台前,和那个半醒半睡的老头连比划带说,满脸喷笑,似乎那个老头就是她的亲大爷。谢玲讲了一会儿,老头儿紧绷的脸松动了,眼睛亮了,不错眼珠地看着谢玲,一会儿,从柜台里拿出两瓶酒,又从瓶子里倒出一堆糖果秤一斤包好,递给谢玲。我赶紧上前付钱。
走出新曙光商店,谢玲满脸都是得意。我问她和老头讲了什么?她一脸诡秘,说道:“不告诉你。达到你心愿就行了呗,你管怎么买的。”
我不得不佩服这精灵鬼怪的城市女孩儿。
回到表姐家,我献上了两瓶酒和糖果,小心翼翼地拿出录取通知书,心里很得意。
看我考取了,表姐开心地笑着,表姐夫对两瓶酒更感兴趣,拿在手中,翻过来调过去地看着……那时还没有假酒一说,表姐夫自然不是检查酒的真假,只是他看酒的眼光有些发绿。
表姐夫看完酒,这才想到我考取了,囔哧着鼻子道:“你小子不懒,三舅把你打发来,就看出你是个苗子。行,我马上给三舅写信,告诉他,我在这里帮你找到了工作,让他放心。”
我知道,表姐夫想给父亲写信表功,但在这时候却是万万不可,但我又不能把我逃离出来的事儿讲给他,只能搪塞说:“信我一会儿写,让他好好谢谢你。”
表姐夫道:“那倒不用。只要你小子好好上学,别惹出麻烦,就算对得起你亲爹了。”
我能考取,表姐表姐夫比我还高兴,表姐特意做了两盘菜——一盘炒土豆丝,一盘炒野菜,另外,还有一盘大酱,一把小葱,我便陪表姐夫喝上了酒。表姐夫对酒的兴趣很浓,喝了两杯后,情绪上来了,讲他的家史,说他爷爷伪满洲国时带着两个儿子来到鹤岗,在此漏粉烧酒,买卖开得很大,整个鹤岗全喝他家的烧酒吃他家的粉条……表姐夫喝多了,念念不忘过去,沉浸在伪满洲国的幻象中……我没有打搅他,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很多现在还不让说的以前的事情。
晚上躺在床上,看着黑乎乎的天花板,我兴奋得难以入眠。想到表姐夫说要给父亲写信,告诉他这一好消息,我又何尝不想呢,可想到父亲在河边对我的嘱咐,“不论你在外面是好是坏,都不要往家里写信。”想到此,我的心又沉到了谷底。
就在这时,不合时宜的事情发生了。
我还没有睡着,表姐住的里屋炕上便发出了咣……咣……咣叽……咣叽……咣咣叽……的声音,声音由小到大,越来越大,简直就是震耳欲聋。我知道那是什么声音。我真后悔买了那两瓶酒,把囔哧鼻子表姐夫烧得忘乎所以,他正不顾一切地发泄着他的欲望呢……我紧紧裹住脑袋,什么也想不下去了,心里却在担心:人高马大的表姐夫,会不会把瘦小的表姐压碎了?但我从表姐兴奋的呻吟中,知道她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