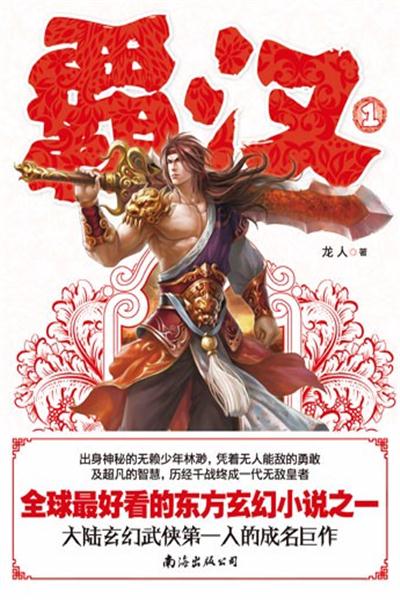在武林至尊的主持下,这酒宴倒还算热闹,表面上也其乐融融。两厢相较,黑道上的人划拳行酒令,弄得热火朝天,而不少正派人士自恃身份,只是相互说说话笑一笑罢了。武林至尊不断地与客人谈笑,倒不管你是黑道还是白道的,众人对武林至尊都极为敬畏。也当真都是只以酒论武,却不提及江湖恩怨武林纠纷。
酒宴结束,客散主归之时,已是月高夜静了,群雄在泰山仆从的相引下各自回房歇息,养足精神参加明日的武林大会。
推浪帮的众弟兄见朴石安返回后方去歇息,凌真儿若不是见夜已深,恐怕要缠着朴石安讲述酒宴中的事。不过朴石安却主动向她说出了,酒席中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他只不过介绍一下所见到的人。当提到尉迟悠云时,他顺便告诉凌真儿那日在景阳冈上遇到的尉迟秋萍实际是个女孩。凌真儿大惊,忆及那日朴石安与尉迟秋萍四目凝视甚久,不禁心中暗暗吃醋,但她也不好放马后炮,只好嘟嘟嘴发发牢骚便了。二人各自回房歇息时已四更天了,明日的武林大会究竟会遇到什么事也只有待明朝天明后方知。现在,抓紧时间休息休息。
泰山顶上,不断地有侍卫巡逻,因此各派的弟子也得以轻闲,勿须放哨。
太阳还未升起来,泰山顶上的客人已几乎全都醒了,纷纷寻一处好地方观看日出。
今日天公很作美,没有乌云遮拦朝阳。
太阳尚未醒转,因此东边天际的一两朵白云也并没有被染色,只是稍微有些红色的影子,有点像婴儿的皮肤,白里透着微红。众人在耐心地等待着。
在泰山上观日出是很过瘾的一回趣事,上泰山的人如果不去观看日出,那简直是白上了一趟泰山。泰山上看到的太阳难道不是别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一轮?这里看到的日出景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的人知道,但他们不说,他们重观此景时依然这般耐心的等待着,显见其诱人之极,很多人是初来泰山,他们当然要大饱一下眼福,因此显得格外激动。
“安哥,快醒醒,天就要亮了!”
凌真儿站在朴石安的床前,喊着他。
原来,朴石安仍在床上做他的春秋大梦,睡得倒挺香的,他还未意识到观看日出这回事,其实他醒了,在凌真儿进门的时候便醒了,但他故意假装睡着。凌真儿在帐外叫喊时,他也不理会,兀自假寐。如果凌真儿直接喊他去看日出,他肯定会一个筋斗翻起来,可凌真儿没有。
凌真儿只是在心中感到纳闷:“安哥今天怎么睡得这么沉?难道他早就起床了?”思忖间她猛地掀开了帐子!
“啊!”她惊叫了一声,上身立刻往床上栽倒!朴石安一把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他故意设下陷阱,就等她按捺不住时掀开帐子,只要帐子一掀,朴石安的双臂便如灵蛇般出动,缠住她的纤腰。
“打扰我的美梦,你说,该怎么罚你?”朴石安一脸戏谑地笑着,手中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
被紧紧地搂着,两人的脸几乎贴在了一起,能清楚地感应到对方的气息和心跳,凌真儿怎还记得要去看日出?她的脸颊顿时红了,心跳加速,美眸似嗔非嗔,娇柔地道:“你想怎么……罚就……怎么罚。”声音是小的可怜,娇躯象征式地挣扎了几下,然后便干脆不动了,一副任君处罚的样子。唉,她本是好心来叫朴石安一起去看日出,可他非但不领情,还要处罚她,真是好心没得好报!算了吧,罚就罚!
朴石安邪邪地笑道:“真的吗?”
凌真儿只觉全身柔软无力,不能垂头,只好假装闭上眼睛,因为朴石安的目光太……那个了!一时之间,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唔!”她总算含糊地吐出了一个字,但那是因为她的小嘴被封住了,她竭力反抗——她还有多大的力气?很快,她便觉得自己仿佛在一点一点地被融化,身躯剧烈地颤抖着,急促的喘着粗气,发出呼呼的呻吟声,双手也由胸前缓缓地不知不觉地挽向朴石安的颈脖——像灵蛇一般。同时,她的小嘴也不知死活地回应着。
唇分。
凌真儿仰脸望去,朴石安那朗如星晨的清澈目光,正炯炯有神地紧盯着她,使她芳心最隐秘之处,泛起了无尽的爱的涟漪。她感到身体如火烧一般灼热,因为与朴石安那亲密无间的接触,他的魅力是如此强大,使她在此刻除了他之外,什么都不愿分神去想。
朴石安看着她那连耳根都红透了的模样儿,搂着这香喷喷、热辣辣,且被他逼得大动春心的绝世美女,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爱念。激动地真诚地说道:“真儿,嫁给我好吗?”
他的声音好柔、好醉人,那么有诱惑力,使她有主动献上樱唇的冲动。啊,他说得是什么?凌真儿霎时惊醒,笑声道:“你……你说……说什么?”
朴石安深情地望着她,柔声道:“真儿,嫁给我,我会好好地照顾你一辈子,爱你一辈子!”
凌真儿身躯猛地一颤,事情来的太突然了,她没有来得及去细想。在内心深处,她愿意与他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现在,朴石安开口求她嫁给他,这的确有些突然,不过二人在一起的时间已将近两年,朝夕相处,她早已视他为自己的丈夫了。她激动不已,很想亲口说出“我愿意”三个字,但女儿家的羞态却使她怎么也说不出口,而朴石安则紧紧地盯着她,含情的目光中藏有期盼。
“我愿意!”凌真儿在心里大声叫道,可是这股气流怎么也冲不出她的喉间,饶是如此,她也已倍感娇羞,仿佛那三字已说出口了似的。她羞赧万分地将红透了的脸儿埋入朴石安的肩膀处,身子不停地颤抖着。
接着,她以极细极柔地声音道:“我……我愿……我愿……意!”她的声音比蚊子发出的声音还要小上两分。
如果,朴石安的耳朵不是生在头上,那他绝对听不见这句话。而事实上,他的耳朵是在头上,而且长得位置刚刚好,凌真儿的小嘴便在他的耳廊外,因此,他听到了这一声应允。
其实,他凭着心灵亦可感应的到,凌真儿的表现不正是芳心暗许吗?
得到这满意地答应,朴石安倒知足了,这才思及真儿这么早来喊床是不是有事?于是,他停止了攻城掠池的行动,按捺住欲念,柔声问道:“娘子,这么早来找夫君有什么事吗?”他毫不客气地以夫君身份自君。
凌真儿显然没有料到朴石安会这般称呼她,顿时娇嗔道:“死宝儿,谁是你的……娘子了?”她亦以牙还牙,不过声音不及朴石安的一半大。
朴石安猛地一翻身将她压在身下,邪笑道:“好哇,看本夫君怎么收拾你!”
凌真儿大惊,若不制止他,那好不容易恢复的一点理智又会陷进这没有尽头的情欲深渊中。忙双手握住在胸前蠕动的两只魔爪,娇喘吁吁地道:“安哥,饶了真儿吧。”朴石安恃强凌弱,要胁道:“那你快说谁是我的娘子?”凌真儿美眸无力地白了他一眼,低骂道:“死安哥,死安哥,你这个色鬼,就知道欺负人家,本姑娘就偏不说!”朴石安也不想太过份,亦怕继续如此会真的占有了她,于是他收回了在她胸前恣意把弄的手,充满着胜利的意味道:“好,好,我投降总行了吧?”
他哪里是投降,整个身体全压在那香软的娇躯上。
凌真儿娇喘吁吁地道:“你快放……放开人家,压着……人家……难受。”
朴石安用嘴轻擦了一下她的粉头,笑着道:“好吧,就暂且饶过你。”遂翻下她的娇躯。
终于得到了释放!凌真儿赶忙坐起并逃出帐外,正想夺门而出,忽然听到外面众人的喧闹声,忆起此行的目的。这才转身对着下床的朴石安急道:“安哥,太阳快出来了,再不去就迟了。”
朴石安正想叫她为自己穿衣,闻言大惊,叫道:“唉呀,这么大的事我怎么给忘了?”当下也顾不上叫凌真儿给他穿衣,拿起衣服便往身上套,三下五除二,所有衣物全部上身,然后向外掠去,当然没有忘记拉着凌真儿的手。
宿舍里不断有人往外走出,他们都是去欢看日出的,但很多人自恃身份,却不似朴石安不顾一切地飞驰。玉皇顶的东端有几十丈宽,但此刻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还往峰下跃去,想找一处好地方观日出。
太阳并不因为这么多人的期盼而加快“爬山”的步伐,也不因还有不少人未赶到或没找着容身之处的人而驻足不前。此刻,东方的天际已被朝霞映红,太阳即将出现。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此刻人们才会那般在乎它的存在。娇阳似火,没有人会去欣赏它,也不敢去看它,大家都没那般好的目力。只有朝阳和夕阳,方才别有韵味。不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倒不如朝阳那般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因此最美的还是朝阳,站在地面上看日出,大家都看得多了,便都想站到高处去看,泰山是个绝好的去处,而且又那般有名气,因此人们常常不约而同的纷纷前来泰山之巅观看日出。
朴石安见崖边站满了人,连一旁的大树岩石上都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四处寻找落脚点。心道:“这么多人都挤在一处,如何观日出?泰山不是有一座观日峰吗?想必那里是观日出的大妙去处,我何不到那里去,反正太阳升起也不是瞬间之内的事。”心念甫动,他向凌真儿说了一声后,便拉着她往观日峰而去。
不少人见朴石安往观日峰奔去,也蠢蠢欲动,但眼见太阳即将破晓而出,怕还未到观日峰便露出头了,于是众人都留在原地。
有一个后到的人见前面都站满了人,根本就看不到日出。心中一急反而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人兵器是一根钢棍,他用力往地上一插,顿是入土一尺,然后他纵身一跃,便轻轻巧巧地单足立在棍头上。旁边的人见状大受启发,都纷纷效仿,没有棍棒之类兵器的人则去折来树枝,金鸡独立,这对于习武之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事。只要屏息静气,气贯一脚,保持身体平衡就可以了,武功稍高的人便如覆平地,丝毫不费力气,不过,如此一来,这玉皇顶——昔日皇帝封禅之处,却要落得吭吭洼洼的狼藉一片了。
朴石安、凌真儿二人的轻功均已达至登萍渡水的境界,从玉皇顶到观日峰路程亦不远,是以他们到达观日峰时所用的时间不足一柱香时间的四分之一。此刻天地间一片祥和,天空中飘浮的云朵都已尽被染成红色,最东边的天际更是殷红似血,太阳将在最白处破晓而出。
观日峰之所以冠名天下,是因这儿是泰山顶上观看日出的最好地方。不过,朴石安上得此峰来,却没有看到别的人,这样更好,难得有一份清静。观日峰上有不少岩石,有人就着天然的岩石雕砌了不少石凳,倒方便了朴石安二人,他们各自选好一张石凳坐上后,静候旭日东升。
太阳确实马上就要出来了,此刻正是将出而未出之时。天地间还荡漾着夜的阴暗,朴石安觉得自己心里有些着急,甚至可说是迫不及待,他知道太阳的出现,将会发出无数道金色的光芒,从而可以散去阴霾之气,仿佛扫尽天下间的邪恶,还它一片正义的天空。朴石安期待这一刻的到来,他也知道光急是没有用的,任何事情总会有它的过程。慢也好,快也好,都是客观不变的事实,不会因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
太阳,他不知见过多少回,有时太阳使人感到温暖,有时太阳使人饱尝暴晒酷热之苦,但唯有此刻,他是如此地期盼太阳的出现。
小时候,他只会去责怪朝阳摧醒了美梦,使他不得人从舒适温暖的床上爬起。
长大了,长久的内心孤独,使他觉得快乐已随婆婆、师父的逝去而消于无形,他更不会在意那朝起暮落的太阳。最多也只会在心里嗟叹道:“可怜的太阳,你也似死一般的孤独。”
现在,他霍然领会到,宇宙何其之大,太阳确实很孤独,但它却始终一刻不停地释放光和热,大地如果失去太阳,那真的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太阳并不孤寂,大地受尽它的恩惠,永远都忘不了它,离不开它。
自从朴石安创立了推浪帮后,除了处理一些帮务外,他本人便很少涉足江湖。虽然推浪帮干了几件义举,但那大多是属下人等的功劳,他只不过发号施令而已,并未像太阳一般竭力地发光发热。
为了解决练武的死结,三年中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能者上居”中度过的,推浪源水度几乎让他摸遍,但依然找不到他要找的东西。师父因为相貌丑陋,虽仗义江湖却常常遭到非议,最终抑郁而终,他为了替师父出气,故意以一张极为丑陋的面具遮拦住原本俊美非凡的面孔,似乎他比师父要幸运得多,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的工过他生事,然而他知道这只是因为他是推浪帮的帮主。在昨晚的酒席之上,他深深地体到了这一点。
“啊,好美!”凌真儿满是欢喜地大叫道。
太阳终于露出了一角。
朴石安虽然心如潮涌,但他依然关注着缓缓升起的太阳。太阳一点点地往上升,他的心只是在太阳乍现的那一瞬间倍感激动,就像他的眼睛只是在太阳刚刚露出一点时觉得耀眼一般。
太阳很红,虽然还只是露出极小的一部分,但发出的万道霞光依然能划破夜幕留下的阴影。
一点点地,太阳似乎很艰难地往上爬,它要到天空中大展风采,即使挣扎得老脸通红,依然不屈不饶。
天地间阴暗的地方随着太阳的缓慢升起越来越少了。朴石安很兴奋,阳光仿佛也照透了他的心府,仿佛他得知自己的内功可凭外力提高时一般激动,又似听到武林至尊对人之俊丑的一番见解时一样高兴。
朴石安干脆站起,尽情地舒展四肢,任如霞的阳光洒遍全身,沐浴在这充满朝气的阳光里,全身有一股难以形容的舒适、畅快!
看着太阳慢慢地升起,朴石安暗自下了决心:“今后要学学太阳,尽自己所能地散发出光和热。”
一时思路畅通,朴石安不禁仰天一声清啸,将心中所思所想尽皆融于其中。
此刻,太阳恰好完全升出,一轮圆圆的红日展现在世人眼前,红彤彤,暖洋洋,怎么看怎么爽,爽在身上,爽在心里!
“阿弥陀佛!”
突然,朴石安身后响起一身佛号,他回头一看,只见少林方丈洪雷大师正盘膝坐在一块大岩石上,深邃的目光直视着他。在朝阳的映照下,他的袈裟仿佛踱了一层金光,宝相庄严,这岂是凡人之身?简直就是佛体!朴石安只觉灵台间顿时为之一静,万事万物都可以不去想,更生起了一股冲动,要跪在洪雷大师面前,向他膜拜,他就像大慈大悲的西天如来佛祖。
洪雷大师面露微笑,道:“朴帮主参透天地与人体的关系,获得精神的坦然解脱,实在可喜可贺。人生天地间,有心者,可与天地争芒;无心者,则只能愈显卑微。天地何其之大,包容万象万物,人只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栗,若能从天地中领悟到精神的力量,即使一丝一毫,也是受益非浅。世人观日出,不过观其特,但若天天观日出,却又会觉得不过如此,他们只把日出当作日出,若能视日出非日出,方可得以摆脱人性的必然束缚。”
朴石安静心聆听,洪雷大师的话并非十分深奥,他很快便领悟过来,只觉心中仿佛看到了另一片天地,一切都是那么神奇。他心存感激,忙以后辈之礼相拜。口中道:“朴石安多谢大师教诲。”
不料,他只觉面前有一股无形气压,使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弯下身去,抬头一看,只见洪雷大师双手合十,气定神闲。朴石安不禁暗自心惊,心知就是勉强下去一点也不行,只好站直抱拳苦笑道:“大师好深的内力!”
洪雷大师缓缓站立,然后飘下巨石,道:“我少林武功之名虽流传天下,实则那是末学,殊不足道,达摩老祖当年只是传授了弟子们一些强身健体的法门而已。身健则心灵,心灵则易悟。所谓武功,不过如斯,又何谓高低?”
朴石安垂首肃穆道:“大师精通佛禅,晚辈聆听数句已是受益非浅,真愿长伴在大师身边。”
洪雷大师笑道:“朴帮主虽与我佛有缘,但尘缘缠身,又岂能摆脱?老衲无法看透朴帮主的面相,只能隐隐觉得你日后必会为情所困。不过,一切顺其自然。佛法曰:佛在心中存。只要朴帮主心有悟性,又哪管身在何地呢?”
凌真儿一直潜心观赏泰山日出的绮丽,她心无琐事,自是以一种自然平静的心来看这一天象,虽无洪雷大师、朴石安二人的领悟,但也觉得心旷神怡,朝气蓬勃,全身自心间涌出无穷令人舒泰的暖意。直到太阳完全升起至发射出的光线颇为刺眼的时候方才收回眼睛和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