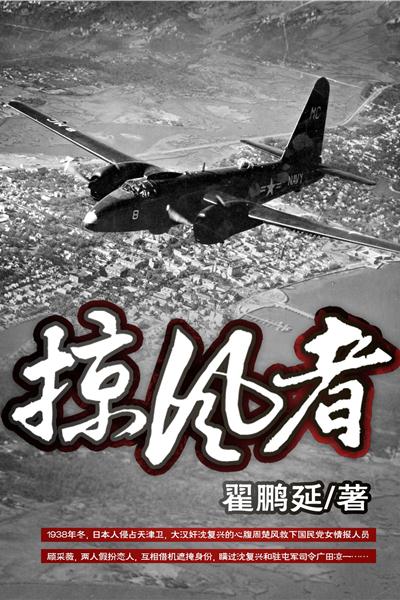徐光启虽然在这儿种山芋,但他一直关心着辽东的动态,多次向朝廷写信,要求当局购置西洋火炮。然而回复是建议很好,就是没钱,现在军队里还欠着饷,哪儿有钱来购置西洋火炮?他便写信给孙元化,要他设法在天主教友中募捐,先买几门,让朝廷能看到西洋火炮在战场的威力,购置火炮的阻力就会小些。所以,当孙元化告诉他这一消息,他高兴地道:“太好了。最近,我认识了一位来华的传教士汤若望,他是日尔曼人,他对我说,一直受到鞑靼人威胁的俄罗斯人,就是依靠先进的火器击败了善于野战的鞑靼人,并且不断向东方扩展。所以,我坚信,我们利用火炮的优势,平定辽东的策略是正确的。”
“老师说得是,但是,要靠购炮来装备我军,太费钱了,所以,这次张焘去澳门前,我要他购买一些有关制造火炮的资料。”
“葡萄牙人不一定肯卖,这次你去北京,可以马上去见汤若望,他对冶炼铸铁很有研究。”
孙元化高兴地:“那我一到北京就去见他。”
山芋烤好了,徐光启拿起一只递给孙元化,孙元化咬了一口,赞道:“好吃,真没想到,山芋还这样好吃。”
“它不但好吃,还有调理肠胃、通便利尿的作用,我那便秘的痼疾,居然被它给治好了,这真是我始所未料。”
孙元化一听笑了:“难怪这次见到老师,比前年精神多了。”
此时,徐光启起身,走到柜前,把一把单管式的望远镜拿了出来,又走到跟着站起的孙元化面前,郑重地道:“初阳,你也知道,这是利马窦在南京时送我的千里镜,我一直用它观测天象,较正历法,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这样可以让你在战时看得更远,让炮打得更准。”
孙元化知道,天文与农事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农事这位老师一直在钻研天文,于是婉拒道:“观测天象也同样重要,老师还是留下自己用吧!”
徐光启坚持道:“不,眼下辽东的形势十分严峻,胜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千里镜应该用到最该用的地方。”
这话让孙元化深受感动,他只得把千里镜接下。
孙元化抵达北京不久,金晓东便在刚买的四合院内的小花厅里招待着冯兆奎。
金晓东是个五十出头、精瘦不高的男人,他的特点是有一双亮而有神的小眼睛,这种眼神在精明的买卖人的脸上常能见着。他是前门大街天云楼饭馆的老板。先前,这饭馆是有些名气,经营多年的老饭馆,只是近年经营不善日渐衰落,最终亏损严重,无以为继,被他以极低的价格盘下,改名为天云楼。
金晓东出生于淮扬名厨之家,身怀祖传的烹饪绝技。中国有句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他不怕饿死,传授了几个徒弟。他结过婚,没有子女,婚后不久老婆就跟别人私奔出走,没了音讯,后来就没有再婚。虽说没有子女是他乐意传授的原因,但主因还是眼光过人,善于经商。知道要想把饭馆做出规模,做出名气,单打独斗是不行的,非得有几个精于厨艺、死心塌地的伙计。因此,几个徒弟对他十分感恩,甘愿为他效力。然而,他更清楚,想把生意做大,在皇城根下玩得转,能赚大钱,这些都还不够,还得另找门路,有个后台。
于是,他就结识了一位神秘人物,作为他的后台。由于他看得准,路子对,很快就进入了发财的快车道。当初他是借款开张的,不久,不仅还清贷款不算,还在京城西四的一条胡同里买下了这幢四合院。这院子空关多年,没人来住,原因是传说闹鬼。早先的房东在这院里娶过几房老婆,可是娶一房死一房。据说,有人还在深夜亲眼见过几个没有脑袋的鬼影儿在院里游荡,让人听着毛骨悚然。以至旧主搬出后,不断降价也没脱手。金晓东胆子大,不怕鬼,他以极为便宜的价格买了下来。其实,他肯出手的原因还不是便宜,而是静,这四合院处在一条僻静胡同的最深处,附近几个院落都是外放大员留在京都的居处,人少院大,老树成荫,相互间从不串门,老死不相往来。
另外,他还觉得这个院子大小合适。他有一位会看风水的朋友,听说他要买这套四合院,过来一看,就说这儿阴气过重,粘上阴气肯定会影响生意,可他不听,事实上他买下这套四合院后,生意反倒更火,节日期间甚至可用日进斗金来形容。
冯兆奎是他刚认识的一位朋友,是个专跑马帮、贩卖人参的霸头。此人一脸横肉,身高马大,很适合在黑道上跑马帮。冯兆奎一到,年近二十、有些姿色的赵八妹便端上酒菜,她是金晓东的女管家。酒是山西杏花村的汾酒,这种酒绵柔不烈,喝多了也不上头,他知道冯兆奎对酒分不清好坏,有二锅头就行,可他怕二锅头太猛,容易上头,不利于商量要事。菜都是肉食,金晓东特为关照八妹,这位客人菜不用多,有肉就行,对他来说什么山珍海味也比不上肥多精少的红烧肉,于是赵八妹精心制作了红烧肉、扬州狮子头和走油扣肉,冯兆奎搛起一个狮子头,咬了一口就连声道好。赵八妹当了几年金晓东的管家,早把他的厨艺学到了家。
金晓东看着冯兆奎把狮子头吃了,又与他碰杯喝了口酒,才道:“冯老板,最近生意做得可好?”
冯兆奎一听,就火了起来:“好个屁!不瞒大哥说,自从那个小皇帝的老师孙老头,当上了什么使……”
金晓东接口道:“兵部尚书经辽使。”
冯兆奎恨恨地道:“对,对,就是这个狗屎,下令不准与满鞑子做买卖,人参也不准进关。我是专在关外收购人参的,这个狗屎可是要断我的财路。”
明朝当局因为兵败辽东,接连失利,在朱由校的请求下,孙承宗兼任了谁都不肯出任的经辽使。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前任中,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孙承宗完全是以国家为重,方才兼任此职。他一上任,除了在防务上做了大量的布置,认为对付金人,进行经济制裁也是一种有效手段。辽东盛产人参,而汉人对于人参进补的功效到了迷信神化的地步,每年的交易量极大,这就成了金人重要的财政收入,于是孙承宗首先把人参列入禁止交易的清单中。
金晓东却道:“难做不等于不能做,量少了,价钱更高,风险大了,做成一笔就能大赚。”
冯兆奎笑了:“金大哥这话可是行家老手的话,难怪金大哥能把天云楼办得如此兴旺。”
“与冯老板相比,小弟还差一截呢。”金晓东谦虚了一句,又道:“冯老板,今天我请您来,知道你在长城的几个关卡都有朋友,还是能出关与满鞑子做生意的,所以我有一笔生意,想请您帮个忙。”
冯兆奎疑惑地:“什么生意?”
金晓东盯着他看了一会,才神秘地低声道:“弄不好会杀头的生意。”
冯兆奎能成为黑道里的大人物,自有他的聪明,只是想了想,就明白了这是什么生意,于是道:“现在从满鞑子那里走私人参,就是杀头的生意,你要是肯出大价钱,杀头从来就不是问题。”
金晓东笑了,现在对他来说钱不成问题。
十三天后,冯兆奎骑着一头健壮的骡子,带着他的马帮队来到兴城堡的门口,一头驴子的背上还搁着两只关着鸽子的鸽笼。兴城堡是明、金交界,由满军占据的城堡。据守在这儿的是金军的镶蓝旗,城堡上插着一面书有满汉两种文字的镶边蓝旗。
这次金晓东出的佣金高得让他感到意外,他就明白,这事的风险也就不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次出关不是在山海关,而在朋友更多、更为安全的古北口,它是长城山海关西面的一个关卡。更重要的是,他事先了解到那儿驻防的部队已经三个多月没发军饷,而山海关是从不欠饷。他深谙钱能通神,越缺钱,钱越管用的道理,花费不多就轻易地摆平了那儿的守备。出了长城,沿着一条小道,顺利地来到了兴城堡。只是因为兜了圈子,多走了两天,可这两天让他省下了两百多两银子。要走山海关的话,多花钱不说,风险还大,所以走得值。何况一路上天气特好,这是近年来这一时段,这条路上少有的好天气。
兴城堡的金军远比明军警惕,冯兆奎到这儿时已是深夜,他还没有靠近城堡,上面就出现一个哨兵,张弓搭箭地大声喝问:“谁?”
“买白皮萝卜的,你去给把总通报一下,一个叫冯兆奎的要见他!”
冯兆奎没等多会,城堡的大门就打了开了,他便带着他的马帮走进城堡。不到天亮,一个金兵小头领就骑着一匹骏马疾驶在路上——他的马背上挂着冯兆奎带来的那两只鸽笼。
赫梅蓝正手握书卷,坐在自己书房的窗边看书,现在她与李永芳各有自己的书房,但她看了一会就撂下书,抬头朝窗外看去,呆望着窗外的天空想,武长春该到北京了吧?她的心中始终牵挂着武长春。她正想着时,明月推门而进:“二格格,兴城堡的把总让人送来一份急件与四只信鸽,说是北京有人让一个跑马帮的带来的,要交给老爷,可老爷刚吃了药睡着了,您说要叫醒他吗?”
赫梅蓝站了起来:“这两天他一直在发烧,没有睡好,先别去叫醒他,我代他先收下吧。”
说着,赫梅蓝跟着明月走出书房,来到了机密室,首先让明月把鸽笼里的四只鸽子送到天井处那大鸽棚内喂些吃食,然后便坐在案前,把装满密件的口袋拆开,略微一翻,发现从明朝当局的邸报到各类机密文件都有。她知道李永芳身体极好,即便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也不曾有过,然而这次却突发高烧,几近昏迷,以至惊动了皇太极,专门派来一位名医,下了几帖重药,方才把高烧压下去。她清楚地知道李永芳的病因,是对她与武长春的事心中窝火,无处发泄,导致肝火过旺、风寒内侵所致。因此觉得对他不起,于是决定先把所有的邸报与密件看一遍,挑出重点,再叫醒李永芳来处理。
当她翻看这些密件时,有一份格外引起她的注意。那是金晓东用那工整楷书写、近似微雕书写的密报,内容是明朝当局任命孙元化出任宁远协守使,协助袁崇焕驻防宁远。对孙元化还专门介绍,他是个基督教徒,对西洋的神机火炮颇有研究,还说此人已经派人携巨资前往澳门购置红夷大炮。
赫梅蓝对这份密报特别敏感,马上联想到小姨博尔济吉特去汤苑那天回去时,不要她派明月护卫,而是举起那把红夷的手火枪放了一枪,把远处树上的鸦巢击得粉碎。那把手火枪的威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推想出红夷大炮的威力必然更为惊人,如果用于战场,定会给祖父的大军造成极大的伤亡。所以把这份密件放在需要处理的密件中的最上面。
当她把这些邸报与密件按照自己的判断,分成轻重缓急,分类放好后,已是日近黄昏。此时李永芳还躺在床睡着,赫梅蓝离开机密室,来到李永芳的卧室,轻轻推门,悄然而进——走到他的身旁,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发现他的脑门汗涔涔的。
李永芳被惊动了,睁开眼睛,大感意外地朝赫梅蓝看着。而赫梅蓝拿起一块毛巾,替他把汗擦了,关切地问:“你出汗了,烧退了,想吃点什么,我去替您去做好吗?”
李永芳的反应不是感动,而是冷嘲:“你今天怎么有点像我的老婆了?”
赫梅蓝微笑道:“朋友就不能关心您吗?何况您是咱们大金国难得的人才,你就是不想当我的朋友,我也有责任关心您呀!”
李永芳支撑坐起后:“你以为,你这种哄小孩的关心,就能弥补对我的伤害吗?”
“那你就把我当小孩,你就不会觉得受到伤害。”
赫梅蓝说时笑得非常可爱,引得李永芳无奈一笑,又问:“你好像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北京那个叫天亮的细作,给咱们送来了一批机密,还让人带来了四只信鸽,当时,我见你刚睡,就代你收了。”
李永芳大感意外地:“天亮还活着?”
赫梅蓝道:“活得很好,他说,他是给带去的最后一只信鸽喂食洗澡时,不慎让它空飞了,让我们错以为他出了事。后来,他一直想与我们联系,没能找到合适的传递人,最近花了一大笔银子,方才找到一个走私人参的马帮头子当他的传递人。”
李永芳一听,兴奋过后又看着赫梅蓝,故意长叹一声:“唉!要是早知道他还活着,武长春就用不着去北京了!”
他是借机刺激赫梅蓝,这种反应完全出自他那泄愤的情绪,无须经过思考。
“不去恐怕麻烦更多。”赫梅蓝也极快地做出回应,女人在斗嘴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什么麻烦?”李永芳故作糊涂地问。
“你心里清楚了,我再说就是多余的废话。”赫梅蓝考虑到他是大病初愈,不想与他斗嘴。
“世界上不可能没有废话。”
“我不想回答你这些废话。”
李永芳知道,这是赫梅蓝在让着他,他也知道这种发泄应该适可而止,终于笑道:“好了,不说废话了,那些材料你看了没有?”
“看了,我初选了一批我认为重要的,等候指挥使前去处置。”
“你倒是挺谦虚的,眼里还有我这个指挥使。”
“我不但眼里有你,且从心眼里敬重你,除了不能跟你上床,什么都能听你的。”赫梅蓝说得坦率而真诚,李永芳无言以对,便离开卧室去机密室。赫梅蓝跟进后,来到案前道:“指挥使大人,左面的文件,我觉得比较重要,右面的可以暂时放一放,供您分析形势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