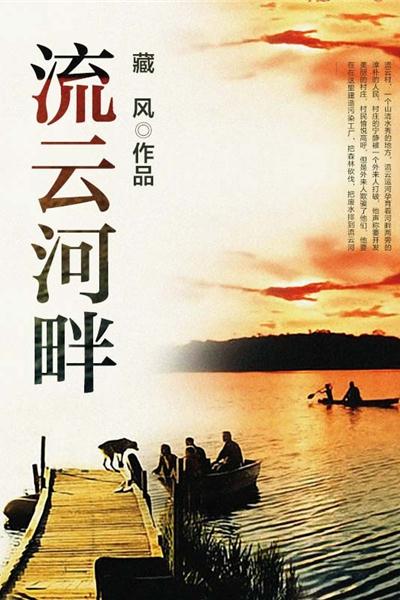1944年2月14日,老天爷将我送到松辽平原上那个叫牛家坨子的小屯子。牛家坨子紧傍着松花江第一大支流伊通河。伊通河是条野河,经常泛滥,但也留下了两岸肥沃的土地。人们为了生存,在大河两岸找些高岗地段定居下来,便有了当地各种色彩浓厚的“坨子”。我家一左一右,就有四五个“坨子”,吴家坨子许家坨子力坨子小坨子……坨子,就是高岗的意思。
我出生那些年,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45年,伪满洲国倒台;1946年,东北率先进行土改;1948年,“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就在我家门前打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因我年龄尚小,并没留下多少印像。
童年懵懂,让我开悟的,却是一窝小狐狸。
时间到了1951年5月。5月,是东北最好的季节,大地从寒冬的蜇伏中苏醒过来,小草萌芽,河流解冻,农民从屋里走向屋外,翻地、撒粪、备垄、播种……一场风,两场雨,麦苗钻出来了,包米钻出来了,高粱钻出来了……几天前,一望无垠的黑土地,眨眼儿的功夫,一片鹅黄暖绿,看得人心里痒痒的。
这个季节,也是孩子最快乐的时候。我和三弟守礼整天都长在原野上,找鸟窝、抓小鱼、捉蛤蚂……这一年,我7岁,守礼6岁。守礼比我小,但比我有能耐,打架敢斗狠,还有一手好弹弓……守礼虽然厉害,却没我的花花肠子多,啥事儿,都是我指挥,他行动。
这一天,我和守礼刚钻进东大甸子,就被在回子坟儿铲地的父母发现了。
牛家坨子,我家住在最东头,再往东,便是一片荒草甸子,大家叫它东大甸子。东大甸子是屯里放猪牧马的草场,也是全屯的墓地。东大甸子东北角,有七、八亩田地,是土改时分给我家的。因田地中间埋了几座回民墓,便被大家叫成了回子坟儿。
父亲一声呼喝,我和守礼乖乖跑到他跟前。父亲停下锄头,看一眼我们小哥俩,板着脸说:“别一天瞎跑,去把东河套的玉米间了。”
父亲的话就是圣旨,我们家,从没有人敢反对他的。
东河套,指的是伊通河的河边儿。伊通河在牛家坨子的东边,屯人习惯叫它东大河。东大河上游百十里远,便是日本人修建的小丰满水电站,每年到了汛期,水库里的水装不下了,开闸放水,我们下游这片田地,首当其“冲”。人们为了阻止洪水冲进家园,在离大河一、二里远的地方,修了一条长长的防水堤,屯里叫大壕。大壕与大河之间空出的这片地带,便是大河套。大河套,是洪水泛滥的缓冲带,里面长满了荒草灌木,也成了狼狐的天堂。土改时,我家虽然也分到了田地,但父亲并不满足,不顾东大河经常泛滥的危险,带领家人在大河套里又开出了十几亩地。
我和守礼一路跑到东大河套。
我父亲敢冒险,是他懂得庄稼生长的规律。他在东大河套种的大多都是高粱,高粱茎杆高,被水泡上十天半月的,水退去后,还能活,耽误不了多少收成。种点玉米,就属于碰运气了。所谓“间”玉米,就是种玉米时为了保苗,每个埯子里点上三粒种子,小苗出土后,拔掉多余的两株,只留一株长粮食。我和守礼到了地中,一顿乱薅,刚到晌午时就把活儿干完了。干完活儿,我和守礼在河边又玩了一会儿,看到晌午歪了,便去找父母回家吃饭。
父母还没走,坐在坟旁休息。他们好像正看着什么?我俩溜到跟前,也没发觉。
回子坟,不知什么年间留下的回民墓地,就像牛家坨子没有一户姓牛的人家一样,牛家坨子,也没有一户回民。回子坟有六七座坟冢,大多塌陷到了地下,长满了荒草。
我们到了跟前,这才看到,父母是在看坟地中间的小狐狸呢。
回子坟中间一座大一些的坟冢,底部被掏出一个大洞,洞口有三只小狐狸崽儿,正在撕扯着吃着一只野鸡。
小狐狸小狗崽儿一样大小,黑黄色,嘴巴尖尖的,小耳朵竖起,尾巴很长,全身油光光的。一只野鸡,被它们吃了一半儿。它们嘴巴上沾着鸡血、鸡毛,还在你争我夺,并不把旁边看它们的人儿当回事儿。
小狐狸的憨态,激发了守礼的野性,他“呼”地一下扑上去,小狐狸比他还快,小屁股一撅,“嗖嗖嗖”全钻坟洞里了。
这时,父母才发现我俩回来了。
母亲责备守礼:“把你能的,还想抓狐狸,它们神着呢。”
回家的路上,母亲嘱咐守礼说:“以后,不要碰狐狸,它们有灵,和它们处好了,能保护人家。”
松辽平原是满金故地,也是萨满之乡,人们崇尚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对狐狸更有许多敬畏,很多人家都供有狐仙牌位,称保家仙。狐仙文化,一直是东北亚文化的一部分。
母亲的话,让我灵光一闪:狐狸神通广大,将狐狸交好了,要啥有啥,想啥来啥,那多好。我将想法同守礼说了,他用衣袖蹭一把鼻涕,深沉地点点头,马上又犯愁了,小眉紧皱说:“咋能讨好它呢?”
“狐狸不是爱吃鸡吗?咱们给它弄鸡吃。”
“我操,你要敢抓咱家鸡,咱爹不把你卵籽儿挤出来才怪。”
我眼珠一转说:“王麻子家不是有鸡吗?”
王麻子是我家邻居,家里养了一大群鸡。王麻子和我父亲年岁相当,三十多岁,长得人高马大,脸型标致,遗憾的是长了一脸麻子,整张脸看上去就像核桃皮一样,坑坑包包的。王麻子是屯子里跳神的,也就是印地安语义上的萨满。农闲时,大家没活儿干了,便有人开始闲得生病了,就有人请他去跳神儿治病。
王麻子神跳得怎样没人说得清?但他跳神跳来一个媳妇,一直是屯里人乐道的话题。
王麻子媳妇叫王大姑娘,和王麻子结婚后,大家还叫她王大姑娘。王大姑娘是王家坨子人,王家坨子离牛家坨子二十五里地。王大姑娘的父亲是个大地主。王大姑娘十五岁那年冲了神儿,光腚儿满街跑。听说王麻子会跳神,王大地主将他请去,王麻子一番哼唱,王大姑娘的“神儿”来了,说王麻子是她前世丈夫。王大地主听“神儿”如此说,又见自家姑娘光着腚被大伙看个够儿,顺水推舟,将王大姑娘许配给了王麻子。
王大姑娘嫁给王麻子后,“神儿”走了,人儿来了。多年后,我帮他家数了一下,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我将主意打在王麻子家,守礼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将守礼叫起来。
我们带着武器——弹弓和泥球,藏在王麻子家墙根下。
天空瓦蓝瓦蓝的,阳光像通透的水,满屯子里滚着。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的柳树、杨树、榆树,捧着一抱抱新绿,将一座座灰突突的泥土房都映绿了。我和守礼无暇感受这份美好,只盼着王麻子家快点放鸡。每天这个时间,我父亲早耪完半亩地了,但王麻子家还没起来。我们等了好一会儿,王麻子家才有了动静。一会儿,王麻子推门出来,看看天,走到墙根儿撒泡尿,回屋叫起几个孩子——老丑子老够子串铃子,爷几个懒洋洋地拿上锄头上地去了。
我们又等一会儿,王大姑娘才起来。
王大姑娘个头儿不高,脸黑黑的长满雀斑,裹着小脚,手中提着一杆大烟袋。王大姑娘的的大烟袋三尺多长,除了吸烟,还能当拐棍儿,也是打孩子的家伙什儿。王大姑娘走出门,也看看天扭到墙跟儿,蹲下撒泡尿,然后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提着烟袋,扭到鸡窝前,烟袋锅一勾,腰都没弯,便将鸡架门拉开了……如此,又为她的大烟袋增加了一份儿用途。
最先钻出的是一只大红公鸡,它看看明光瓦亮的天,“呕喔”一声啼叫,叫声未消,唏哩哗啦,十几只母鸡全钻出来了。这些鸡出来后,拍打拍打翅膀,在院子里趸摸一圈儿,看没啥吃的,一溜小跑儿钻出院子,到街上打食去了。
王大姑娘打了个哈欠,回屋补觉去了。
鸡到了当街,四处散开。
我四处看看,屯子里除了阳光滚动,几只狗趴在各家门前,一个人影儿没有,便冲守礼点一下头儿。
守礼皱着眉头,拉开弹弓,对准就近的一只芦花母鸡,“嗖”的一弹弓,只见那只芦花鸡“啪”的一下跳起来,接着又“啪”的一声落到地上,伸伸脖儿不动弹了。
守礼打弹弓百发百中,天生的一样,也难怪,后来能成为小兴安岭有名的猎手。
看到鸡被打死了,我跑过去,将鸡包在衣服下摆,转身就跑,身后,守礼在后面紧紧跟着我。
我们一口气跑进了东大甸子。
绿油油的大甸子里,除了鸟鸣虫叫和一群猪在远处拱动,一个人影儿都没有。我放心大胆地拿出鸡,守礼的弹丸正中鸡头。我将守礼好一番夸奖,他很高兴,一边抹着鼻涕一边二哥长二哥短地叫个没完。
我们踩着甸子上斑驳的绿色,一会儿便到了回子坟儿。
我将死鸡放在狐狸洞口,和守礼离开一段距离,躲在一蓬干草后,观察着洞口的动静。
鸡味儿传进了洞里,不久,三只小狐狸全从洞里钻出来了,看到鸡,马上奔过去,拼命撕扯着,一会儿,血肉模糊,鸡毛飘得满地。我和守礼再也蹲不住了,凑到它们跟前儿。小狐狸的劲头全在鸡上,小眼睛虽然看着我们,并无敌意。守礼不安分了,他一伸手抓住一只小狐狸,小狐狸想跑,守礼拿起一块肉送到它的嘴边,它竟就着守礼的手吃起来。我一看,也伸手抓住一只,它也在我的手上吃了起来。
一只老母鸡,很快被它们吃光了。
我们征服了小狐狸,我们随意用脸贴它们的小脸,用手抚摸它们柔软的小肚皮,它们似乎很喜欢,讨好地伸出小舌头舔着我们的手指。
我们不知玩了多久,它们的父母——两只火红的大狐狸跑回来了。大狐狸有半大草狗大,拖着长长的大尾巴,黄中带红,在太阳下光芒闪闪。它们对我俩现出敌意,脊毛竖起,尾巴拖在地上,呲牙咧嘴嘶叫着,围着我们转圈子,随时准备发起攻击。我怕惹恼它们,和守礼赶紧放下狐狸崽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回子坟儿。
第二天,我和守礼故伎重演,在王麻子家又打死一只鸡。
这是一只黑色的老母鸡。或许是受萨满文化影响,认为黑色不吉利,从小我就对黑色天生反感,不敢走夜路,不愿穿黑衣服……我对守礼打死黑鸡有意见,让他再打一只,他眼睛一翻,说道:“得了吧,咱们也不能太祸害人了。”
我只好抱着黑鸡来到了回子坟儿。
我将鸡放到洞口,等了半天,小狐狸一只也没有钻出来……想来,一定是昨天大狐狸受到惊扰,带着小狐狸搬家了。
狐狸没出现,一个惊天动地的声音出现了——“小兔崽子,原来是你俩将我家的鸡,偷这儿来了。”
我抬头一看,黑如铁塔的王麻子,铜钱般罗列的麻子脸,变成了紫红色,鸡蛋大的牤牛眼,正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俩。我第一个想法就是逃,递眼色给守礼,但我错了,这时才看到,王麻子身后还有他两个虎羔子儿子——老丑子老够子,另外,还有一个母夜叉姑娘——串玲子。这三个家伙,都是打架不要命的主儿,他们从几个方向将我俩包围了。
老丑子骂道:“揍死他们,揍死这两个小杂种。”
老丑子刚骂完,老够子给了我一拳,一拳就把我打倒了,老丑子又上来加上两脚。这时,守礼疯了一样,瞪着眼睛,握着拳头,“啊啊”叫着冲向老丑子,没等挨边儿,被老丑子一脚踢倒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抬起头对串玲子说;“串玲姐,我们赔还不行么?”
串玲子比我大三岁,平时我就叫她串玲姐。串玲子野是野,但长得漂亮,我对她颇有好感。没等串玲子说话,王麻子开腔了:“小兔崽子,你们赔得起么?走,带他们找他老子张海怪去。”
张海怪是我父亲的绰号。我父亲是辽阳人,当地有一句顺口溜:辽精海怪秀岩大脑袋。意思是说,辽宁的辽阳、海城、秀岩这三个地方,人都特别精明。按理说,我父亲生在辽阳,叫辽精才对,乡下人胡按马槽,将我父亲叫成了海怪。王麻子和三个孩子押着我们,拿着罪证黑鸡和一把芦花鸡毛,来到了我们家。
王麻子有意让全屯人都知道,刚到我家大门口,就扯开跳神的嗓子喊起来了:“张海怪,你给我出来。”
晌午了,下地的人都回家了,听到喊声,我爹我妈大姐二姐都出来了。
我爹看是王麻子,面色不悦地问:“嚷嚷什么,谁得罪你了?”
“谁得罪我了?问你两个小崽子。昨天偷了我家一只大芦花鸡,今天又偷了我家一只大黑鸡。这两只鸡,都是下蛋最好的鸡,他们打死喂狐狸去了。”随着王麻子痛不欲生的陈述,老够子扔下黑鸡,老丑子扔出一把芦花鸡毛。
我父亲看着罪证,铁青着脸问我和守礼:“真是你俩干的?”
守礼马上将我出卖了,低头小声说:“二哥让我打的。”
父亲什么都明白了,一脸杀气,突然抡圆了胳膊,“啪、啪”两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我脸上。我眼前金花乱冒,耳朵嗡嗡响,这时,他又飞起一脚将我踢趴下了。按理说,打孩子到这个份上也就行了,但父亲并没有停下,他的脚带着风声,在我身上踢来踹去,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皮球,在他脚下滚着……痛触中,就听妈妈大姐二姐哭喊着拉我父亲,但我父亲好像疯了,还在不停打我。
我终于明白了,为了两只鸡,他不打死我是不会罢休的。我放弃了抵抗,也抵抗不了,只等着父亲将我打死。
迷糊中,救星来了,是我外婆还有刚吃午饭的乡邻们。乡邻知道我父亲的脾气,没人敢上前劝,但我外婆不怕。外婆也有一杆大烟袋。外婆不由分说,一烟袋锅刨在了我父亲头上。父亲见有人打他,一看是我外婆,这才住下手来。外婆不依不饶,又上前打了我父亲两个耳光,开始骂人了,骂的却是王麻子。外婆骂道:“你王麻子不是人,你流落牛家坨子,我不收留你,你都饿死了。多大点孩子,打死你两只鸡,烧你房子毁你地了,还打上门来了?”
王麻子被外婆镇住了,嚅嗫着道:“我哪打上门来了,只想说道说道,谁知道张海怪这样狠?”
“张海怪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说道说道,那就是要孩子的命。”
王麻子开始道歉,说:“大娘,我也是一时气糊涂了。大娘都说话了,那还说啥了。鸡我不要了。走,回去。”
王麻子灰溜溜地走了,大家看没热闹了,也散了。
我母亲怎样把我抱回屋的,我已经不知道了。
我在炕上躺了三天。三天来,母亲一直看护着我,每顿饭,母亲都煮个鸡蛋,剥好皮偷偷塞给我,看我大口小口地吞咽,母亲总不忘提醒我一句:“慢点吃,别噎着。”说完,又劝我:“你不要生你爹的气,谁让他是你爹呢。”母亲如是劝我,反过来,忍不住又小声骂了:“打孩子哪有这样狠的?真是胡子根儿。”